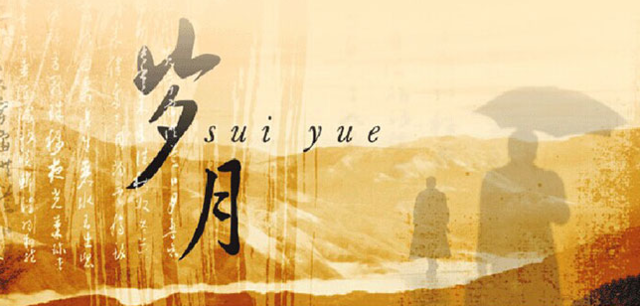铁道兵文苑
拐杖哪去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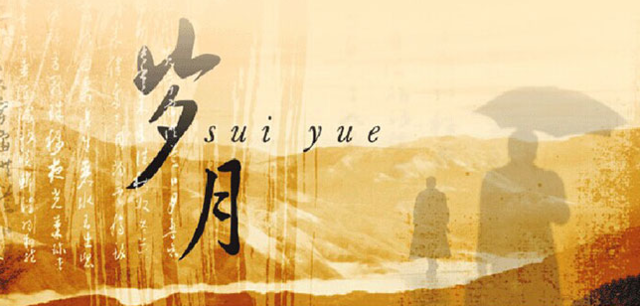
“布谷、布谷……”布谷鸟也抒情唱着晨曲,似乎在和雄鸡报晓遥相呼应……
忽然,从坐北朝南的主卧房间传来奶奶一声感叹:哎,哎呀,拐杖咋不见了呢?
哦?不至于吧!拐杖还能跑到哪里去了呀?
一叶知秋的脑屏幕说,年过九旬的老太太,会不会去了老爸赋诗的那个“朝夕亭”:景观池,四面环水;/一座精巧小桥,金鱼游弋图案。/清风亭,八根石柱,/一个个艺术圈,鹅卵石编织花瓣。/夕阳红,五行操;/一样样,来来回回。/古筝伴,旋、旋、旋……/舞蜿蜒,转、转、转……/昨日,这“老小孩”瞧天气晴朗就信步青春家园绿色长廊蹓跶,一时来了兴趣步入景观池中间的清风亭跳起了“拐杖舞……”极有可能是跳累了,随手将拐杖放在亭子里长长的木椅边,然后和几位老邻居有说有笑走着走着,就忘记带它回家?
“ 这不可能?”
忘了吧,去年春节你开小车带上奶奶俺和你爸去广东,一路经东莞、过广州,进深圳、访惠州……在“华阳湖湿地公园”“五羊石雕”“世界之窗”留影;穿过“南昆山”“双月湾”,上深圳第一高楼平安金融中心,夜游珠江时拐杖都不曾离手。
可不是吗?字里行间一气呵成沒有丝毫的停顿,更没有一丁点犹豫真是心无片云,心如止水。
试问:如果手上沒柱拐杖,那俺怎么进的单元门和家门?
哦,咋忘了?奶奶的记忆可真不差,明明白白知道自己家的钥匙结结实实绑在拐杖上。
于是,祖孙两人一道从主卧、次卧,又由卫生间、厨房,再从饭厅至客厅,然后又把急切的目光久久盯在阳台……
二遍、三遍过去了,依然不见熟悉拐杖的踪影,难道它长了翅膀飞走了?
会不会在客厅沙发、茶几底下,以及玄关的鞋柜上、电视柜侧面,还有大门、阳台、卧室门背后,尽管二人不遗余力的观察、分析寻觅,依然找不见日夜从不离开的得力“助手”。
别看奶奶嘴里讲不急不急,却一遍又一遍手眼身法步左看前行、右瞧后退……
此时,想起今年两个“黄金周”,我和父亲陪奶奶赴贵溪的白鹤湖、鹰潭的方特乐园、宜春的明月山、新余的仙女湖、黄马的凤凰沟、鄱阳湖的鲤鱼洲打卡……也没见老太太拐杖失踪过。于时,再次静下心仔细思索一番,既然奶奶已确定将拐杖带回家了,丟是肯定没丟。那有没有可能,花香不在多,雅室何其大的哪个角落会特别喜欢和这“宝贝”谈天说地呢?
说话间,老太太一拍大腿自说自话“有啦、有啦!”一天三次雷打不动口诵心至念书的地方,不就在阳台上的东侧转椅的周围吗?
只见,老人家心静如水踱着方步再次来到阳台以东,坐在转椅上用手朝上扶了扶新配的老花镜,将视线聚焦一盆盆上下排列整齐的绿箩、三角梅靠墙夹缝间端详……
终于,呈现一个再也熟悉不过的特写镜头,我也三步并作两步靠近,祖孙二人同时对视笑了笑……仅仅才露出小半个手柄的那根闪着褐色光泽拐杖赫然在目。
不会吧?奶奶的“伙伴”怎么会闯进我昨夜的梦境呢?
记忆显示:夏日一个黄昏,洪城武阳古镇涂钦广场西边,一位戴银色宽边眼镜年轻人,凝视一只金色的小蜻蜓,翻着筋斗云调皮飞进莲花池塘,时而盘悬、时而穿梭一朵朵盛开的荷花之间,随意将三对长长的脚逗留一支粉红清水菡萏上摇呀摇……此情此景的看客正是奶奶手上那根神气的拐杖,悠闲地迎着夏日凉风摇头晃脑地诵读宋朝杨万里的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日夜相伴的拐杖啊拐杖啊,真不知说你什么好?怎么也没想到,你竟然躲在这陌生的世外桃源悠哉游哉看风景?
二0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作者简介:涂 倞(笔名: 滕实),“铁二代”,大学学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营养师,平凡而普通的驾驶员,喜爱传统文学、诵读和健身,时常写一些散文、随笔、感言,以人生当“如水之静、如水之明、如水之善、如水之韧”勉励自己,注重读书、行路、阅人、思悟。
照片由作者提供
编辑: 老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