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说,现在父亲大部分时间都会卧床睡觉,已很少要求出去。即便偶尔被推出去,走不了多远,也会要求回来休息。也许处于病中的父亲,平时想出去的要求大多被否决之后,说也无用,不如不说,习以为常罢了。 由此可见,一生自信而风云乡里的父亲,一旦生病,仅这一点小小的要求也得不到满足,他还有尊严,心中的痛苦非常人可以体味得到。
我回家后父亲有了一些明显变化,每天早上起床会要求我陪着他,给他穿衣、洗脸,然后给他喂饭,吃饭时情绪平和,进食量大多尚可。遇到饭菜可口时,还会给我伸出大拇指表示赞许。这是基本失语后的父亲,所能做出的对最高评价的基本表达。次日近午,父亲对我示意推他出去转转,我就推着轮椅上的父亲出了院门。天气晴好,阳光如练,田里不多的几陇麦子被晒得金灿灿的,可以看见远处有收割机在轰鸣中前行,周围一些乡亲在配合机器忙碌着。更多的地块都栽种了猕猴桃和大樱桃,还有一些洋蒜种子等经济作物。昔日这个 季节里热火朝天的麦收插秧的场景,再难寻觅。在这个世世代代以出产贡米闻名遐迩的北方水乡,那一流清冽甘甜的石头河水,前些年被饮水吃紧的省城西安引走后,水乡的美丽与灵气随之消失殆尽。当地已基本无水可用。曾经遍地清泉喷涌,渠水不断的河滩地带水价奇贵无比,水稻种植渐次销声匿迹,现如今据说种粮的农户已经凤毛麟角了。
推着父亲,穿过一片柿子树和杨树林,过了穿村而去的姜眉公路,下 了一道缓坡,路边一小片菜地里,看到多年未见穿了一身道袍,头顶挽着长发髻的喜财哥,正在心无旁骛,飘逸地锄着地里的杂草。和喜财哥打过招呼,推着父亲继续东行,不料大口井边的路被挖开了一条沟渠,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载着父亲的轮椅推了过去。已显老态的田娃哥在地里刨洋芋, 地里有几小堆中不溜的洋芋和一些近乎干枯的洋芋的枝蔓。田娃哥似乎已记不起我是谁了,和他打过招呼,走出了好一段路时,才听见他在自言自语唔咙着我的小名“喔——是满吟”。仿佛才思怫过来。到东水田了,这里 过去算是队里最靠东的一片水地,由南边的钟家院子下来呈阶梯状,直到我和父亲停着的路边,有好几十亩,再往东就是塬上的旱地了。过去米价好,旱地不被看好;而今猕猴桃和大樱桃等经济作物,则更适合旱地栽种,旱地倒成了抢手的香饽饽。父亲坐着轮椅,眼睛始终闭着,每到一处,我便会问父亲所处的位置,父亲稍一睁眼便能轻而易举说出所在田块的名称来。由于是田间车路,少量沙石铺就的路面凹凸不平,父亲无力支撑的身 体,就靠在轮椅的靠背上,推着走时,随着颠簸,父亲的头便不时轻触在靠背的金属靠栏上,我于是用一只手推动轮椅,腾出另一只手护着父亲的后脑部,以免触疼父亲 ;同时还需弯下腰身,用自己的身体为父亲挡出一片阴凉,直到有树荫时才能停下轮椅稍作休息。
东水田地势较低,又是古河道,水分丰沛,田边水草茂盛,仔细看时,竟都是水芹菜,一丛一丛,郁郁葱葱嫩绿鲜活,禁不住顺手搙了几把,放在车架上。这是野生的水草,小时候打猪草水芹菜是绝好的目标。也可食用,据说对调理高血压等病症极有裨益,父母都患高血压,做成凉拌菜佐餐,既鲜美 又利于康复。
在一片树荫下稍作歇息,见父亲已有困意,问时,果然说要回去。恰 逢周末,下午小妹红儿带着上一年级的外甥凡凡回来了。见妈已做好晚饭,就又告诉妈水芹菜的做法,很快竟做成了一大盘上桌。 开始没人敢吃的水芹菜不一会便所剩无几了,尤其妈听说可治疗高血 压,吃了不少 ;小外甥凡凡不甘示弱,一个劲说好吃,夹着吃个不停 ;我 给父亲也夹食了一些,好像也对胃口,竟多吃了不少饭。
父亲,已无力长久睁开眼来关注这个世界,却每天要我带他出去转两次,或乘汽车,或轮椅。母亲说这是很久都不曾有的了。以往回来,一帮朋友、同学、战友轮番盛邀相聚,轮到陪伴父亲的时间就寥寥无几。这次回家一周,除了和几位挚友老师聚了一次,推掉了其他所有应酬,专心在家陪着父亲。作为儿子,作为唯一从小离家,几十年在外打拼的儿子, 我从父亲苍白消瘦的脸上读懂了几分欣慰、舒心与满足,这不正是作为儿子的我所最最需要的吗!
这次回家陪父亲,很少出门,也没有刻意拜访朋友,但有挚友宽余的问候,好友宝仓的关心,有与发小金海的开怀畅饮。发小大龙四儿,连续两晚自几十里外赶回来相陪相叙,每至凌晨才回去休息。他俩是我唯一一 篇小说的主人公。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常年离乡漂泊的游子难得的温馨。 假期有限,陪伴有期,而亲情深邃而绵长,只望父亲的身体平稳,不出大的问题。只希望能多一点时间来陪伴我苦难深重的父亲,希望老人家平平安安。
2012 年 6 月 19 日 郝家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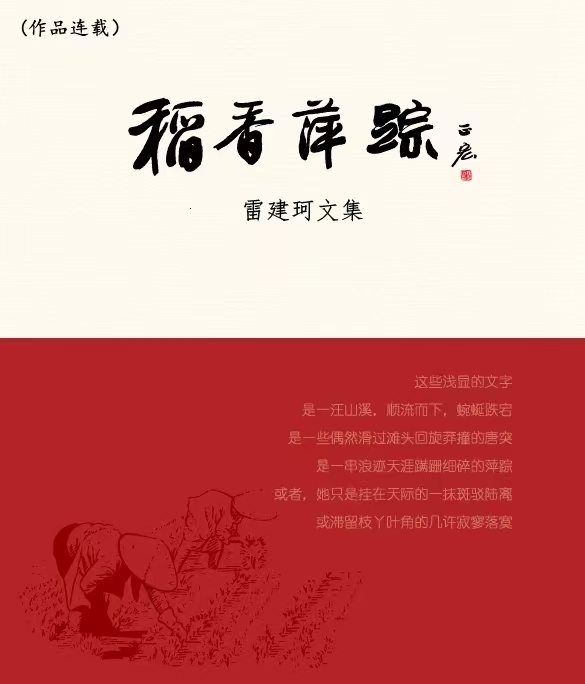
依稀旧梦
我的二伯父雷志有,于公元二〇一四(古历甲午)年正月十八日辰时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七岁。谨撰此文,以资缅怀。
刚过了甲午新年,正月十五后的第三天,苦难深重的二伯父,永远地走了 ;从容地离开了这个对他老人家来说,已经毫无留恋的世界。我是在二伯父故去后第二天的午后,从哥哥打来的电话里得到这个噩耗的。其实前两天还曾打电话给妈妈,特意问起过二伯父的情况。妈妈说还是在年前的时候,曾听二妈说起过,早已病情严重的二伯父,说是想吃 上一顿搅团,都两年多没吃搅团了。正月十五那天,妈自己突发奇想,竟然一个人费了好大的气力,打了一锅搅团,端了一些送到不远处的二伯父家。然而,此时二伯父的情形已不容乐观,几乎神志不清,水米不进了。直到此后的第三天早上七点二十分去世,二伯父尽管期盼了两年多漫长的时日,尽管老人家很算得上子孙满堂,功德圆满,却终于没有吃上一顿家里最普通不过的家常饭——搅团。
二伯父生于20世纪的一九二八年,即民国十七年的二月二十八日。当 时军阀混战,内乱不断,常有土匪乘着黑夜下山来打家劫舍。此后不久尚 在襁褓中的二伯父便遭受了人生的第一次劫难。
二伯父出生不久,民国十七年的一天,一伙外地土匪有十几人,乘着天黑前来劫舍。听到动静,祖父迅疾将祖母和年幼的大伯、襁褓中的二伯 母子三人,藏到后院猪圈的屋顶上,回身隐蔽于竹园边的水沟里伺机出手。 一帮黑衣蒙面的土匪,何曾想到这家主人会有如此高强的武功,随即大大咧咧破门而入准备实施抢劫。可还没等站稳之际,便被从天而降的祖父一阵拳脚打得七零八落,四散而逃。而被祖父事先安置在猪圈房顶上的祖母却由于过分紧张,不慎竟将襁褓中的二伯父掉进下面的猪圈之内。所幸房低土软,襁褓厚实,二伯并无大碍。而此时二伯尚未取名,经此一跌,祖父遂给二伯父取名曰“猪娃”。这名字作为乳名也便伴随了二伯父的一生。
祖父母二老先后育有两个我的伯父、父亲和两个姑姑共五个子女。民国二十四(1935)年,残暴的民国政府大肆敲诈、鱼肉百姓,给乡民下了残酷毒辣的所谓“毒条子”。
国民党政府就是用这样恶毒下作之策,来威逼百姓出壮丁、纳钱粮, 否则就封门闭户,不许回家。为了不使年仅 12 岁的大伯被抓去做炮灰,被逼无奈的祖父母,只能强忍悲愤,将年仅七岁的二伯以十块响元的价钱卖与张家大户,十块响元则全数上缴民国政府,以抵废丁之资。
老张家是钟家院子好几代的殷实富足人家。到了张老爹这一辈,成了 独传,唯剩张老爹一人苦苦独撑。眼看张老爹就要年过四旬了,老两口还 没生下一男半丁,苦苦叹息之下,只好守着个独女过活。女儿名凤莲,视 若掌上明珠,疼爱有加。在张家老爹看来,自己世代富足,有地有钱,却 是后继乏人。而隔壁雷家自川上下来便穷困潦倒,却代代人丁兴旺,就是 和自己年纪相仿的雷老爹(指爷爷雷明德)竟然连续生了三个儿子,还个 个生龙活虎,且聪明伶俐。时间一长,难免心生嫉妒。张家老爹并非恶人,对国民党残酷的“毒条子”政策亦颇有微词。雷家几代光棍,家徒四 壁,日无隔夜之粮,身无分文之银,他老雷家如何拿得出那些数量不菲的 白花花地响元!难免会有几分眼红,也还是心存几分恻隐之心的。其实聪 明的爷爷奶奶早已看出老张家的心思,然而在当时民国时期“天下衙门朝 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的黑恶统治下,穷苦百姓啼饥号寒,穷困潦倒, 无以为生,唯有被统治阶层任意宰割的份儿。此时此刻,苦苦努力等待,几近绝望的张家,似乎真的看到了机会和希望,不失时机地差遣门脚前来 放话,并软硬兼施,许下诺言,说如果雷家把三个儿子中的任意一个卖给 张家,他们老张会像看待亲儿子一样给吃香喝辣,疼爱如若己出。
祖父母在“毒条子”加身,孤苦无助的紧急关头,经过了长时间的痛苦煎熬后,经过询问已经稍稍懂事的二伯父,终于做出了人生中最为艰难残酷的决断 :暂且把年近黄口的二伯卖与近邻的张家为子,以此来换取全家老小的性命,躲过这一劫难。
那天夜里,一家老小围抱着泣不成声的瘦小的二伯父哭作一团。心里最为凄苦的奶奶,面对即将永远离开亲生父母还是个孩子的二伯父,早已哭哑了声音,流干了眼泪,却一直紧紧搂着浑身瑟瑟发抖的儿子,絮絮叨叨,翻来覆去重复着到人家后,如何做人做事,如何不要争强好胜劳累坏了身子,如何改改牛脾气少受打骂,如何常偷空多回来瞅瞅。苦难深重的一家老小就此度过了一个漫长而异常煎熬的不眠之夜。年仅七岁的二伯,从此不得不离开从小相依为命的父母兄弟和小妹,独自去相邻的张家,在 一个完全陌生的家庭里面对完全陌生的一切。时值七岁年纪的二伯,当时要承受多么巨大的无助的凄楚。作为亲生父母的爷爷奶奶,眼睁睁看着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宝贝儿子,快要长大成人的宝贝儿子,就要永远离开亲人离开这个朝夕相处了七年的家,唯有对这个黑暗世界的满腔怒火和悲愤 ;还有自小一起同甘共苦,一起长大的哥哥弟弟们,此时此刻,在他们 心中无不充满着无尽的痛惜和不舍。
自二伯父进入张家,便犹似一只羔羊进入了魔掌。二伯父自小脾气直爽倔强,心地善良,长期在穷苦家庭生活。虽说清苦,却也其乐融融。在 这个人生成长的反叛期的孩子,突然被迫进入那样一个人人优越,恣肆高贵的家庭,更激发了二伯素来养成的反叛的个性。进而在张家形成了一个和家庭水火不相容的尴尬情形。胳膊自然拧不过大腿,因此二伯父在老张家难免腹背受敌,动辄被斥责体罚,时时挨打受骂,吃尽了苦头。
而近在咫尺的父母兄弟,每天在亲人被困苦海之时,却每每只能敲碎 了牙齿往肚子里咽,偷偷为二伯的苦难遭遇流了不知多少辛酸的泪水。唯有在偶尔相见时送上一些宽慰贴心的嘱咐。后来老张家唯一的女儿凤莲长大成人,张老爹眼见日益长大的二伯桀骜不驯,似乎难以托付继承家业,便为女儿招了一门渭河以北的女婿,名叫张志银。张志银后来终于不负张老爹的满心期望,先后为老张家生下了一双儿子,使得老张家的子嗣家业得到了传承,这是后话。老张家为独女招赘后不久,张老爹老两口便因年老相继撒手人寰,驾鹤西游去了。
即将长大成人的二伯父,顿然失去了根基,一时间成了张家小夫妻的眼中钉肉中刺。如此凑合着,已经成人的二伯又在老张家苦苦支撑了几 年。眼看着过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然而此时的老张家,却根本没有人真正为他操心张罗婚事。时刻记挂着这个身陷苦难境地儿子的父母,私下里曾想让二伯父重新回到雷家来。然而此时由于解放战争接近尾声,国民党军队穷途末路,兵员匮乏,四处抓丁拉夫近乎疯狂,接二连三地来乡里强拉壮丁去内战前线充当炮灰,二伯回家里只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此后,新中国成立,二伯父经人介绍去了岐山唐家岭的一户人家入赘。然而好景不长,生性倔强的二伯,因实在受不了在这家被人驱使,寄人篱下的屈辱生 活,此后不久便愤然离开唐家岭,重新回到张家。
此后不久,二伯又一次经过好心人介绍,在本村一任姓人家入赘为婿, 就此安顿下来。任家为人善良厚道,任家老人对直爽勤快的二伯父敬如上宾,二伯父和二伯母小两口也琴瑟和谐,举案齐眉,情投意合。至此,二伯父才真正脱离苦海,过上了正常人幸福美满的甜美生活。
二伯父一生育有二子四女,到中晚年均是举家幸福和睦,其乐融融。其中二儿子和小女儿分别学有所成,事业兴旺 ;其他子女也都生活安适,子嗣顺遂。二老儿孙满堂,心满意足,只是出于对老张家的养育之恩的回报,以及做人的道义和责任,二伯父及其子孙均随老张家的姓氏,始终没有更改。
再说民国31 年(1942),尚未成年的大伯,曾三次被抓壮丁,暂时投入设在眉县县城的预备营关押,以备集结遣送。每次都是由祖母东凑西借来一些银圆去县上交保领回。有一次,大伯父被抓后,刚被祖母交保领回未几,又被抓走了。走投无路的祖母,又一次急疯了。怀里揣着的几块大洋,是刚刚磕头作揖,求爷爷告奶奶从左邻右舍处借贷来的,加上又是小脚,心急火燎跑得满头大汗的祖母,哪里还顾得上自己有多么饥饿劳累, 一心只想着被关在预备营里受苦的儿子,只恐怕稍有差池就被送到战场上去送了性命。身心俱疲的祖母,好不容易又一次来到关着刚成年的大儿子的预备营,哪承想,看管大伯父的差官,经奶奶见面一说,还没来得及送上事先准备好的几块大洋,竟被那差官拽到大伯身后,指着毫发无损的大伯父压低声调说道 :“好娃娃,老实娃娃,快引(方言 :带领之意)回去安顿好,别让娃再待在家里了。” 见事情出乎意外的顺利,奶奶恐生变数,也顾不了许多,便赶紧拽了儿子的手,颠着一双早已跑得生疼的脚,娘俩三步并作两步跑出县城, 来到一处僻静之所,迫不及待询问儿子个中缘由。原来大伯被抓进预备营后,独自一人被关在一间既昏暗潮湿又脏乱不堪的土房子里。差官安顿好大伯父后,临走锁门前撂下一句话:“小伙子,门后面有笤帚,把房间仔细打扫规整好,明天一早我来查验。” 大伯自小勤快,等差官刚一走开,也顾不得自己还饿着肚子,便在门后面找到一把秃头笤帚,径自仔细收拾起房间来。刚扫了几下便发现墙角落处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远处油灯豆焰微弱的光亮下,泛着一丝青光。出于好奇,大伯便弯下腰凑近捡起来时,感觉像是银角子,拿近油灯仔细一看果然是枚一角的银角子。心想许是谁不小心遗下的,随即把这枚银角 子,仔细放在屋角靠墙安放油灯的破旧不堪的木条桌上,再继续打扫房间, 不曾想打扫完房间,竟然在一堆垃圾里找到了 11 枚一角贰角不等的银角子。大伯由此寻思着,如若谁一时不小心,遗失一枚,最多两枚银角子还算是常理,这一下子毫无由头地捡了这许多银角子,应该绝非偶然。更何 况差官临走时好像是特意嘱咐让仔细打扫房间的。如此一番思量之后,心里随即豁然开朗。虽说自己连续被国民党抓丁,现如今仍被关在这里身不由己,前路未卜。恍恍惚惚看着破条桌上散乱着的一堆银角子,回想着亲一个妇道人家,自己已连续多日四处颠簸,这刚出魔窟又入牢笼。要交保金放入还需要更多的银圆。本来一个穷困潦倒,几口人常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苦人家,现如今早已家徒四壁,刚经历过几次三番的倒借折腾,还哪里凑得出几块大洋啊!再一想,这哪里是捡的银角子啊,分明是人家差官在试验咱的人心呢。咱人穷志不短,咱再怎么艰难也必须堂堂正正做人。想到这里,大伯父心里顿时豁然开朗。回身把刚刚打扫出来的垃圾扫进门后墙角的一只破筲箕里,再来到破条桌前。大伯父盯着灯盏时明时暗的光焰下,那一堆幽幽泛着青光的银角子,定睛注视良久。随即开始缓缓动手,把那一堆散乱的银角子,一枚一枚在手心里码好,又把这些沉甸甸的银角子,整整齐齐摞在了破条桌中央的油灯盏下,大伯这才长长出 了一口气,心底不由得生出几分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坦然。伴着窗外昏暗的夜色,伴着一丝深秋的寒意,伴着一腔年轻的百结愁肠,伴着难忍的咕咕作响的饥饿,大伯和衣在墙角地上的麦草秸上进入了苦难的梦乡。 一腔饥肠辘辘的大伯父,正要对眼前一碟白花花的蒸馍下手时,突然之间被一阵杂乱的叫喊声惊醒,原来是在做梦。此刻,刚从睡梦中惊醒的大伯父,见天已大亮,差官正站在那方破条桌边,先是露出一脸满意的表情看着整齐干净的地面 ;紧接着,差官一双犀利的眼光又随之扫向破条桌中央的那一沓银角子,稍停片刻。随之又投来一丝疑惑的神情,接着露出几分不易觉察的狡黠的神色,便伸出右手拇指,指着那一沓银角子,缓缓地问大伯道 : “哪里来的这些个银角子啊,小伙子?” “扫地的时候扫出来的”大伯父回道。 “扫地扫出来的,怎么不自己收起来啊?” “这些银角子不是我的,我不能要!” 见大伯父的回答里透着几分倔强坚定的口吻,差官一边满意地点着 头,一边一股脑儿将这些银角子揣进了自己怀里的荷包。 原来这看管大伯父的差官,是个好心人,眼见大伯父年纪虽小却慈眉善目,帅气利落,顿生好感,便有意试探一下这小伙子的品行。如表里如一的话,便决计做一回好人,索性放了大伯父回家 ;如若不然,便毫不留情,照章行事。如此一来,才有了这么一出让奶奶和大伯父都深感意外的惊喜。 领着大伯父出来后,奶奶直接让大伯去了秦岭深山里的高码头一户人家里扛长工去了。
2014 年 2 月 28 日 郝家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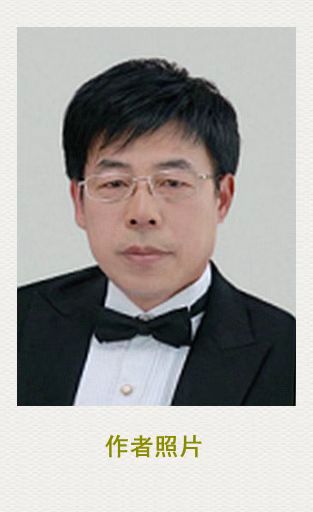

编辑:岁月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