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道湾十一号故事多
我们三位虽属两代人,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很敬重伟大的鲁迅先生。爱屋及乌,因为热爱鲁迅,所以对于与先生相关的事物就格外关注,比如他在北京的故居。
鲁迅先生从1912年至1926年,也就是他32岁到46岁期间在北京工作生活了近15年,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青壮年时代。15年里,先生在北京长时间居住过的宅院有4处,分别是:宣武门外绍兴会馆、西直门内八道湾胡同11号、西四砖塔胡同61号和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21号(今西二条19号鲁迅博物馆)。这四个地方,我们都先后拜谒过,其中尤其钟情于八道湾胡同11号,因为这里发生的故事最多。

八道湾胡同很窄,曲里拐弯,因此得名。八道湾胡同11号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作为鲁迅先生与其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的旧居,所以声名远播。 1912年5月5日,鲁迅来到北京,住在“山会邑馆”,即绍兴会馆。这一年8月,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并任佥(签)事。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引起了巨大反响。住在绍兴会馆期间,鲁迅还写下了《孔乙己》和《药》等著名小说。

鲁迅到北京五六年后,工作基本稳定下来,就决定买一个院子,把母亲接来奉养。从1919年2月开始,鲁迅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外出看房,先后看了数十处,最后定下八道湾胡同11号院。
八道湾胡同11号,是鲁迅4处故居中比较特殊的一处,它记载着鲁迅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许多珍贵记忆,也发生了许多值得人们记取和回味的事件。根据我们走访相关人士的讲述,结合查询的一些资料,顺便记录几个故事如述:
故事一:周家的佣人
家住八道湾11号院内的张大妈,曾是周家的佣人。准确地说,张大妈的姑妈真正是鲁迅一家的佣人,而她只是后来接班给周作人夫妇当保姆。
当年鲁迅买下八道湾11号院不久,周家一大家12口人团聚在此,家里就顾了多位佣人,有司务、车夫、洗衣工、杂工、保姆等,张大妈的姑妈被招来做了保姆,一直做到解放前夕。那会儿,张大妈正值妙龄女郎,曾跟着张瑞芳、黄宗英等人一起拍电影,跑龙套,当时跑龙套的还有牛犇。后来张瑞芳、黄宗英她们要去上海,约他们一起去,牛犇跟去了,而她因为家人不同意就没去。
1949年周作人出狱回到八道湾11号以后,张大妈的姑妈对她说自己岁数渐大,希望她接替自己给周作人当保姆。在她和周家双方同意下,这事就定下来了,一干就是许多年,直到1967年周作人去世。
张大妈从小就听姑妈讲发生在八道湾11号的许多事,觉得很有趣味,一一记在心头。
张大妈十分健谈,虽文化程度不高但知识面很广,记忆力超强,简直就像一部活生生的京城现代史。张大妈还提到,她接受过30多个国家记者的采访。
令人惋惜的是,张大妈家庭生活境遇十分不如意。她迈入老年后,身边只有一个下了岗、离了婚、生了病的女儿。女儿不能生育,为了排遣寂寞,就领养了一个外孙女,一家老少三代女人,靠政府救济过日子。后来女儿因病不治而亡,外孙女知道自己的身世后,扔下姥姥找亲生父母去了,张大妈孤苦伶仃一人度日。尽管如此,老人家从来没有抱怨过老天的不公,见人总是乐呵呵的,和蔼可亲。
张大妈对八道湾11号院感情至深,几十年生死守望,还为保护它多方呼吁,四处陈情。

故事二:周家欢聚八道湾
张大妈听她姑妈说,鲁迅先生买下11号院后,经过几个月时间整修,便和二弟周作人、弟媳羽太信子先行搬入了新居。1919年12月,他回到故乡浙江绍兴,将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及三弟周建人、弟媳羽太芳子接来北京,全家欢聚在八道湾11号院。
这个院子是一个典型的三进四合院。鲁迅之所以要买这么大的院子,主要是考虑院子大一点便于孩子们玩耍。中院有三间高大的北房,母亲鲁瑞和朱安分别住在东西两间,中间的堂屋是全家人吃饭的地方,西边三间房是鲁迅居住和写作的地方。周作人夫妇和周建人夫妇分别住在后院和前院。院子里还有一个种着荷花的水池。
住进八道湾的第二个年头,周家兄弟就开始逐渐离散,最先离开的是小弟建人。因为他没有合适的工作,需要两位兄长资助,自己过意不去,妻子羽太芳子又埋怨他没本事。周建人只在这里住了一年多,就离开妻儿,告别大家庭,启程去上海谋事了。
周建人到上海后,在商务印书馆获得了一份工作,安顿好后就张罗着准备接妻儿过去。但妻子羽太芳子不愿离开八道湾的大家庭,主要是不想离开姐姐信子。周母对芳子说,女人嫁了人就应该跟随丈夫,哪能不跟丈夫跟着姐姐的?芳子仍然不听。无奈,周建人只得听由妻子自己作主,他将每个月的收入除留下个人生活费外,大部分都寄回八道湾补贴家用。后来,周建人同曾经是绍兴女子师范学校学生的王蕴如结婚,事实上与留在八道湾的羽太芳子脱离了婚姻关系。
故事三:水池里上演“鸭的喜剧”
张大妈家位于11号院东北角,她家门口有一个当年留下的坑。大妈说,这个坑就是以前的那个荷花水池,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曾在水池里养过鸭子。
1922年,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到北大教世界语,暂时借住在八道湾11号鲁迅家中。爱罗先珂虽是盲人,却多才多艺,既是著名诗人,又是音乐家。他会弹琴,会唱歌,闲暇之时与家中的孩子们玩得很开心,关系很融洽。
爱罗先珂曾在泰国、日本、缅甸、印度等国漂泊,也游历过我国一些省份,他很喜欢在大自然里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他嫌北京太寂寞,尤其是夜晚,听不见昆虫、青蛙的叫声,便买来了蝌蚪放进荷花池里喂养。后来,爱罗先珂又委托鲁迅的家人买来几只小鸭子,鸭子在水池中嬉戏,顿时院里增添了许多生气。
夏日的晚饭后,爱罗先珂常常坐在院子里,弹着优雅而略带伤感的曲子,与鸭子“嘎嘎”的叫声和青蛙“咕咕”的鼓鸣组成一支奇妙的交响乐。鲁迅看到这样的情景,顿生灵感,便以爱罗先珂在八道湾居住期间的这段生活为素材,创作了那篇著名的散文《鸭的喜剧》。
故事四:阿Q的诞生地
八道湾11号人文蕴含丰富,辐射面也十分广泛。
《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很看重鲁迅和周作人的文才,他曾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鲁迅居住在八道湾11号期间,许多友人都希望他多创作一些文学作品,这些友人中就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等。鲁迅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的出版,陈独秀出力甚多。
八道湾11号中院的西侧,有一间房是鲁迅的书房,这里后来被称为“阿Q”的诞生地。
要说阿Q艺术形象的诞生,离不开一个叫孙伏园的文学编辑。
孙伏园是鲁迅的绍兴同乡,著名的副刊编辑、散文作家。他接替李大钊编辑北京《晨报》副刊以后,就想找几个大牌作者给副刊打打名声。孙伏园首先就想到了鲁迅,就到八道湾11号向他约稿。
据鲁迅回忆,“他来要我写一点东西,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突然想起来,晚上便写……”
从1921年12月4日开始,《阿Q正传》在孙伏园编辑的《晨报副刊》上连载。鲁迅说,孙伏园“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
著名记者曹聚仁曾记述,我们能看到孙编辑的催稿艺术可谓“已臻化境”:他“不仅会写稿,会编稿,而且会拉稿;一脸笑嘻嘻,不容你挤不出稿来。我们从周氏兄弟的随笔中,就可以看到这位孙先生的神情。圆圆脸,一团和气。跨进门来,让你知道该是交稿的时候了。”
鲁迅被孙伏园“折磨”了两个多月,产生了把连载中的阿Q结束掉的想法。但孙伏园认定:“《阿Q正传》似乎有做长之趋势,我极盼望尽管宽心地写下去。”说过此话,孙伏园便出差去了,由另一位编辑代理编务。鲁迅在1922年2月12日的报上发表了“大团圆”一章。等到3月底孙伏园返回北京,鲁迅笔下的阿 Q已经被枪毙一个多月了。看来,如果孙伏园不出那趟差,《阿Q正传》也许会写得更长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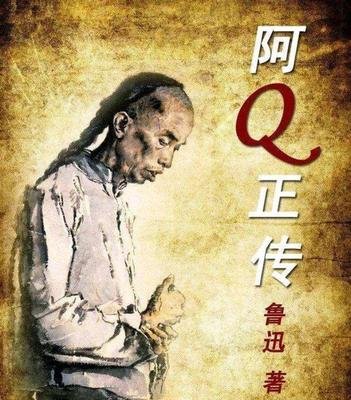
在八道湾11号期间,鲁迅还写了《明天》《一件小事》《风波》《故乡》《端午节》和《社戏》等作品。
故事五:兄弟反目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悬案和鲁迅研究的一大谜团,被认为是现代文学三十年最大的隐痛。本来最为亲近的兄弟两个,最终竟会绝交,成为参商,以致终生不再往来。让人不解的是,两人绝交之后,都绝口不提此事,怨恨之深,难以释怀,切肤之痛,难以愈合。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张大妈的姑妈在周家20多年,亲身经历了周家兄弟反目的那段日子,姑妈不只一次私下给她谈起这件事。按张大妈的叙述,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鲁迅从老家北上北京的同时,周作人夫妇从日本回到了家乡绍兴。鲁迅除了在经济上继续接济他们之外,开始对周作人的事业操心费力。周作人翻译著作,鲁迅为他联系出版单位;鲁迅还带着弟弟一起以共同的笔名发表作品。为了提携周作人,鲁迅把花费了大量精力编成的《会稽郡故事杂集》,用“周作人”的名字出版发行。1917年,蔡元培上任北大校长,鲁迅向他推荐周作人,蔡元培欣然应允,聘请周作人做了中文系教授。
1919年冬天,周氏兄弟结束长期的寄居生活,买下了八道湾11号。经历了多年的骨肉分离,鲁迅终于兑现了青年时代的承诺,兄弟三家大团圆,有钱同花,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一同赡养辛苦了大半辈子的老母亲。此时,鲁迅和周作人已是思想文化界的明星,两人的月薪加起来超过500大洋,生活无忧。
八道湾这所大宅子名义上的主人是鲁迅,但周家的财政大权却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掌管,鲁迅和周作人每月的收入都交给信子打理。周建人还在学习,没什么收入,需要花销大家都觉得理所应当。
遗憾的是,信子不善管理,还养成了乱花钱的坏习气,有时竟出现开销紧张的情况。周母对此很不满意,便对鲁迅说:“老大,你给老二媳妇说说,节俭一点,一大家人过日子,不能这么大手大脚。”鲁迅便跟信子说老太太不高兴了,让她注意节俭。鲁迅也让周作人提醒一下信子,改改坏毛病。信子表面并不言语,但心里生出一股怨气,认为是鲁迅在老太太面前挑拨,从此记恨起这位大哥。
恰在这时,周作人告诉鲁迅,说他和信子商议要把岳父岳母从日本接来一起住,鲁迅不同意,这下惹得周作人和信子都不高兴。信子还大声告诫孩子们,不要搭理那个“孤老头”,不许吃他的东西,让他冷清死。
有一天,周作人回到家里,信子突然在他面前哭哭啼啼。周作人问怎么啦?信子竟说你去问你那大哥吧,做兄长的这么不检点。原来信子竟跟丈夫说鲁迅对她非礼。
周作人一听,火冒三丈,不问青红皂白,提笔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周作人来到鲁迅的书房,见他正在伏案写作,“啪”的一声将信拍在书桌上,扭头便走。

鲁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拿起信一看,信封上赫然写着“鲁迅先生”。鲁迅拆开信,只见信是这样写的: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情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看完信,鲁迅心中五味杂陈,家里竟会发生这种莫名其妙的事,作为长子,他真不知道该如何向老母亲交代。
鲁迅让佣人去把老二叫过来,要他和信子把话说清楚,但周作人坚决拒绝了。鲁迅一时感觉束手无策,不知怎样平息这场家庭风波。
中国有句老话:“家丑不可外扬”,经过一阵思来想去,鲁迅为了息事宁人什么也不想说了,决定搬出八道湾。
经过一番寻找,鲁迅选定了西四南大街砖塔胡同61号,8月2日,鲁迅和夫人朱安住进了这里。后来有一次鲁迅回八道湾取书籍和用品,竟然还遭到周作人夫妇的追打。
至于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反目的真正起因是不是张大妈所说的那样,不得而知。因为兄弟二人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发生了如此让人震惊的事情,只是把它看作普通的家庭纠纷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事件迅速在思想文化界发酵,各种传闻、猜测不绝于世,众说纷纭:
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后来说,父亲信中所谓“我昨天才知道”,指的是他舅舅羽太重久住在八道湾期间,亲眼看见“哥哥”与“弟妹”拥抱在一起之事。而有人认真地推算了一下时间,指出鲁迅周作人兄弟反目时羽太重久根本就不在北京。
有人则举出周作人后来自己的解释,他写字条给鲁迅原只是请他不再进后院就是了。言下之意,并非真的要与哥哥决裂。
日本有学者则分析出现这种传言的原因是:周作人的后代被鲁迅的家人、特别是被许广平批评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喽啰、奴隶,自己没有辩解的机会。于是,置非议于不顾,将屈辱感、愤怒感、怨恨之心都汇集在一起,制造了这个具有攻击性的流言。
另有一种说法,鲁迅与周作人翻脸仅仅源于“拆信事件”:他们二人有许多共同的朋友,有时候朋友写信来,虽然信是写给两个人的,但收信人却常常只写一个人。有一次,一个日本朋友写信来,信封上写的是周作人收。鲁迅将信拆开看了,不料信里的内容是写给周作人一个人的,所谈之事与鲁迅无关。第二天早上鲁迅将信交与周作人时,他突然板起面孔说道:“你怎么好干涉我的通信自由呢?”于是两人便大吵起来,后来矛盾越来越深。
还有其他种种说法,有些言之凿凿,有些似是而非,有些则一听便是无稽之谈。不过,兄弟俩相互的忌恨越来越深,几乎闹得势不两立,这是不争的事实。
鲁迅曾在《〈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中愤恨地称周作人是抢劫者,八道湾成了盗窟,题记用词也够有分量。
后来的许多评论者认为,鲁迅一贯对周作人有恩,周作人“赶走”鲁迅是忘恩负义。要算经济账的话,鲁迅吃亏不小:八道湾住宅的产权,本归他们兄弟共同所有,周作人却独自占之。周作人听信妇人之言,更是糊涂透顶。总之,周作人的做法很不对。
故事六:周作人保护李葆华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与周氏兄弟很友好。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处以绞刑后,扬言要斩草除根,追杀他的后人。周作人与北大同仁商量,将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隐藏到了八道湾11号自己家中,后送他去了日本留学。
事情的经过是,1927年4月初的一天,周作人等人在北大“沈门三杰”之一的沈士远教授家就餐,这其中有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不料第二天李大钊就被张作霖逮捕。预感情况不妙的周作人和沈士远商量,就让李葆华住在了沈家,没有回去。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时年38岁。不久,周作人与沈士远联系,冒险将李葆华接到了自己家里居住。
李葆华是李大钊长子,时年18岁。他在周家所住的房间,正是后来张大妈的家。这期间李葆华得到了一家人悉心照顾,不过,周作人还是时时刻刻为他的人身安全提心吊胆,生怕走漏风声。过了一个多月,周作人觉得这么下去终究不是办法,就和友人商议将他送到日本留学。就这样,李葆华化名杨震得以前往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
1933年,李大钊先生的夫人赵纫兰不幸离世,周作人将他们的长女李星华安排到北京孔德学校半工半读。后来,李大钊的次女李炎华来到北京,也得到过周作人的周济。李炎华的爱人侯辅庭是共产党员,一度被当局拘捕,事后也是周作人出面,疏通关系后将他保释。
李大钊长子李葆华建国后先后担任过水利电力部部长、安徽省委书记等职务。晚年李老在接受采访时,证实了周作人保护他们兄妹的事实。周作人与李大钊、沈士远曾有过在北大一起工作的经历,周作人主动营救老友的子女,足见他的友善,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闪光点。鲁迅对周作人的仗义之举也曾大加赞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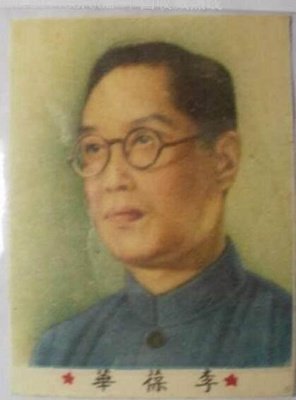
故事七:周作人与张大妈
周作人因为在日伪机构服务的汉奸行为,1946年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胡适等人出面说情,改判为15年。此时周作人已年过花甲,自觉判15年无异于无期,于是让太太羽太信子找人疏通,希望再改判,以便早日出狱夫妻一起过一段幸福日子。周作人此时竟想起了已经去世10年的哥哥鲁迅,让信子去求助于鲁迅生前的朋友。信子说她这时不能借鲁迅的名义求人,毕竟他们做过对不起哥哥的事。想来想去他们突然想到了当年与周作人一起在北大当教授的李石曾,通过李的游说,再次减刑到10年。
1949年,南京政局岌岌可危,胡适等友人又趁机为他暗中疏通,当年1月26日,江苏高法同意周作人保外就医将他提前释放。在临迈出老虎桥监狱的当天,周作人在那间监室内写下一首古体诗《拟题壁》:
一千一百五十日
且作浮屠学闭关
今日出门桥上望
菰蒲零落满溪间
被释放的翌日,周作人去了上海。这时,胡适劝说他一起去台湾,并表示愿意说服蒋介石对他既往不咎,但他拒绝了。
8月14日,周作人从上海抵达中国人民解放军管治下的北平。因为不了解八道湾的情况,不敢贸然回家,所以暂时住在太仆寺街朋友家。两个月后的10月18日,周作人在儿子周丰一陪同下,回到了阔别三年多的八道湾11号家中。
就是在这个时侯,张大妈经姑妈介绍给周作人当了保姆。
回到北平的周作人,暂时没有工作,生活没有保障,这时他想起了自己曾经的学生毛泽东。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经常去听周作人、胡适等教授讲课,还曾到八道湾11号登门向周作人求教。1920年4月7日的《周作人日记》中写道:“毛泽东君来访。”毛泽东拜访胡适的事也有记载,《胡适日记》1920年1月15日写道:“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想到这些,周作人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长信,作了一些检讨,也为自己的过去作了一些解释。周恩来将这封信转呈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于是,经文化部和出版署出面,安排周作人在人民出版社编译室工作,按月发稿费,生活有了保障。为此,周作人对毛泽东主席的大度十分感激。
周作人虽然也深度介入过政治,但他从骨子里就是个文人,性情温和,还有些懦弱。周作人的人生跌了两个大跟斗,一是与哥哥鲁迅闹翻脸,二是为日伪效力当了汉奸,两次都与听信妻子羽太信子的话有直接关系。周作人夫妇虽然晚年常争争吵吵,有些琴瑟不谐,但还是相处了50多年,直至羽太信子1962年去世。
张大妈给周作人夫妇当保姆期间,主仆关系相处很融洽。张大妈称呼周作人为二先生,叫羽太信子二太太;周氏夫妇则随孩子叫张大妈阿姨。
张大妈的丈夫是个理发员,周作人理发的事都由他包下了。1952年初,张大妈夫妻俩喜得爱女,他们高兴,二先生夫妇也很高兴。张大妈说:“二先生学问大,请您给女儿取个名字吧。”周作人慎重其事地取来纸笔,沉思片刻说:“孩子出生在春天,就叫春英吧!”说完提笔在纸上写下了“王春英”三个字。张大妈是个有心人,认为这是二先生送给女儿的珍贵礼物,将这份手迹一直保存着。
张大妈随手保留的与周作人相关的物品还有一些,其中有一件“宝贝”很特别,那是一张欠条。本来,周作人每个月都按时给张大妈发工钱,从不拖欠。有一阵在图书馆工作的儿子周丰一因故被停发了工资,家里开销顿时紧张起来。他们第一次拖欠了张大妈的工钱,只得先给开一张欠款的白条。
“文革”期间,周作人受到冲击,被红卫兵批斗,身体和心理遭受了双重打击,精神状态和身体素质每况愈下。
1967年5月6日中午,张大妈为周作人熬了一碗玉米粥端到他床前,他照例吃得干干净净。下午两点多钟,周作人下床解手时突然晕倒,等隔壁邻居发现时已经没救了。这一年先生82岁,张大妈为他料理了后事。
故事八:八道湾11号的结局
八道湾11号后来成了一个大杂院,人们只顾居住,很少人关注它的命运。只有张大妈一直热心呼吁要保护它,希望将它定为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物保护单位。张大妈说,11号院不仅仅是鲁迅的故居,这里还留下过毛泽东、蔡元培、郁达夫、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名人的足迹,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
附近赵登禹路一带开始规划商业开发时,要拆除八道湾胡同的传闻风声日紧。张大妈心急如焚,有机会就向人讲保护这处文物的意义,有人认为她是多管闲事。当时,张大妈在11号院里有三间产权房,要是拆迁可以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补偿,然而她不为所动,一心想保护这处鲁迅故居。虽然其中有故土难离的感情因素,但我们不得不说老人家的思想觉悟也是令人敬佩的。
为保护八道湾11号院,张大妈还去找过舒乙,请他出面游说。舒乙是积极主张保护八道湾11号的,他说,现代的北京作为一个政治之都,文化之都,聚集过的名人非常多。而名人们又大多不只一处旧居,每一个都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不现实。但八道湾11号地位特殊,在纪念和研究鲁迅方面有着重要价值,应该以一定方式加以保护。后来舒乙多次去北京市文物局陈情,听说文物局答应将这里以“鲁迅著书处”的名义作为准文物单位加以保护。
若干年过去了,八道湾11号的命运终于有了一个令张大妈和许多有识之士感到满意的结局:为建设阜成门内金融街的需要,2009年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搬迁至西直门内,八道湾胡同11号宅院被圈到三十五中新校园内。遵照上级指示,院落整体保留,进行整修,以“周氏兄弟旧居”的名义保护起来,并辟为学校的课外课堂。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的前身是1923年由李大钊、邓翠英等创办的志成中学,这是一所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著名学校。百年来该校秉承“有志者事竟成”的理念,精心育人,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宋平、王光英、李锡铭、邓稼先、王光美、王岐山、陶西平等。
历经沧桑的八道湾11号终于有了一个令人欣慰的归宿。如今,三十五中将志成传统和鲁迅精神作为学校的宝贵财富加以继承、发扬。学校还聘请鲁迅的长孙周令飞为名誉校长,更增强了当代学子与文学大师的情感联系。
“周氏兄弟旧居”不但是学校的一个特别课堂,也成了一处面向社会开放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它像一位阅历丰富的历史老人,站立在世人面前,向大家讲述着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一群杰出人物和一段不朽的传奇。
(作者车文婧: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编辑
蒋跃渊: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教师
程更新:解放军画报社原副社长)
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开门见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