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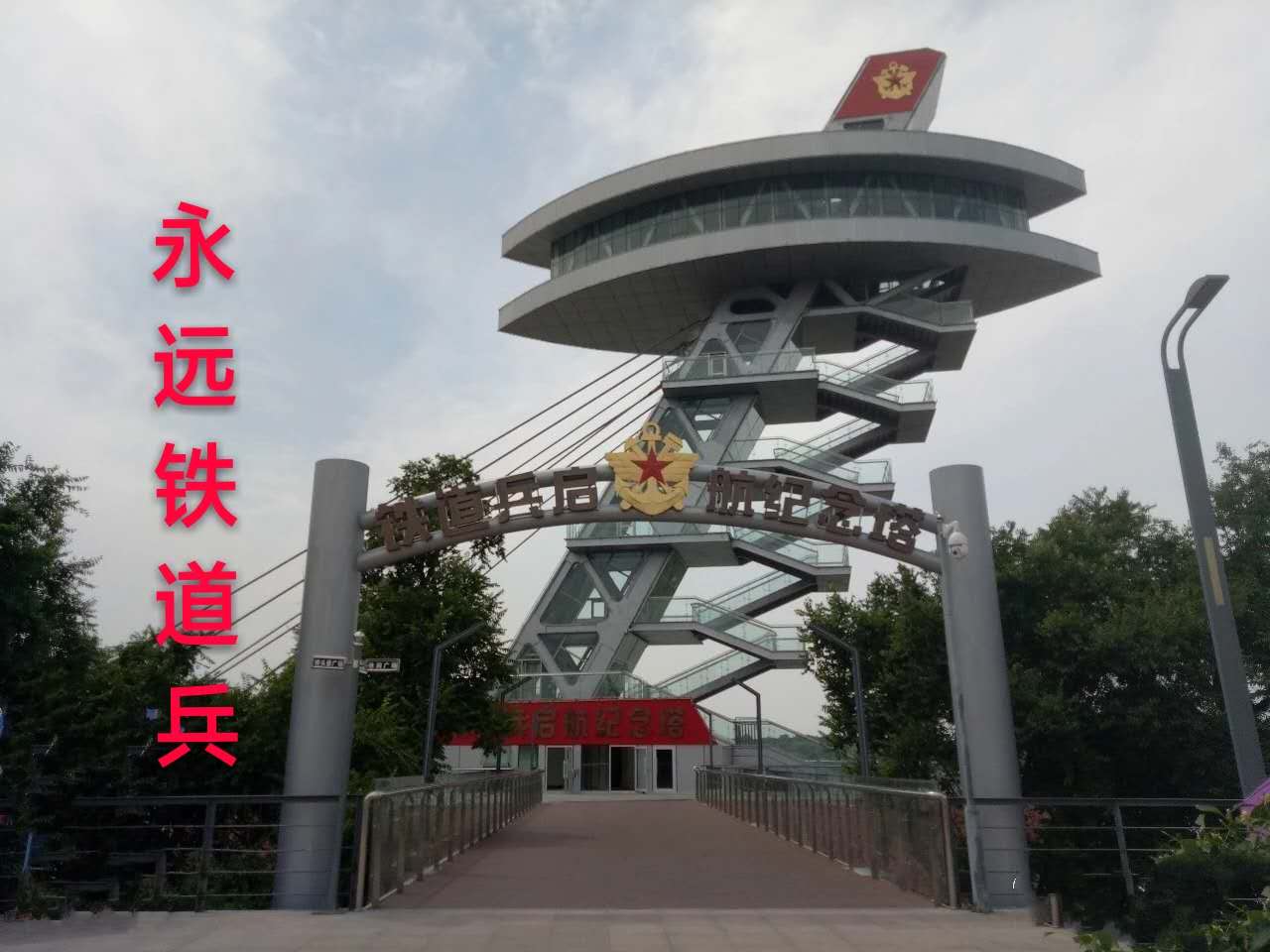

父亲在“应抗”的烽火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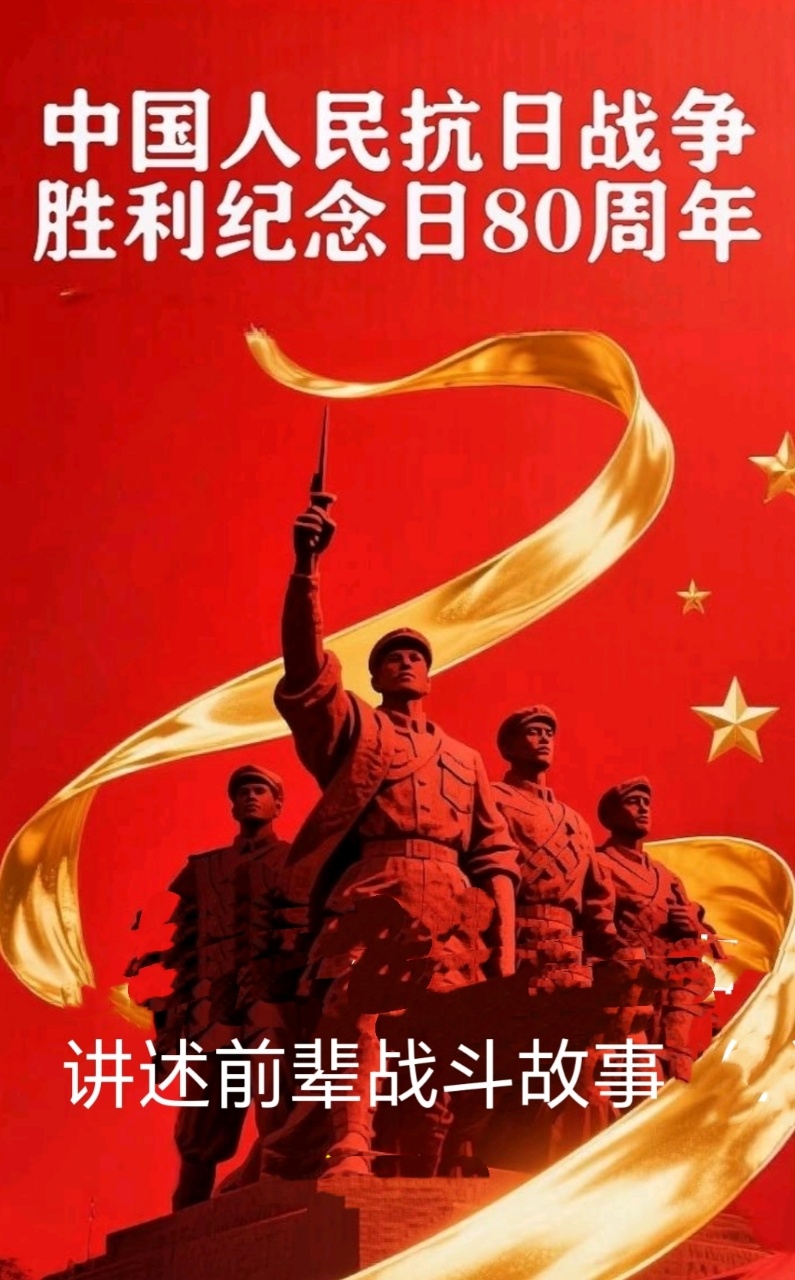
口述/许平安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我重读父亲许子威的回忆文集,那些关于抗战的峥嵘往事,再度浮现眼前。
父亲许子威,湖北应城人,1908年生于贫苦农家。1925年考入湖北省立医科大学。次年北伐军攻克武汉,他受革命思潮感召,投笔从戎,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第六期),并于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随叶剑英率领的军官教导团南下广东,参加广州起义,曾任红军第四师党委书记。
汤池训练班:鄂中”小抗大”
抗战爆发后,父亲返回家乡应城,投身救亡运动。1937年10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得知,辛亥革命元老、无党派人士李范一正在应城汤池创办“新农村改进合作示范合作社”。原来,李范一不满时政,辞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职务,举家迁居到应城、天门、京山三县交界处,偏僻得“鬼不生蛋”的汤池开荒造田搞起了“新农村改进合作示范合作社”。董必武遂萌生借助汤池场地培养抗战力量的想法,遂联系另一位辛亥老
友、时任湖北建设厅厅长石瑛,邀李范一来汉晤谈。这一谈可谈出来一桩大事。不久,李范一携合作社副经理许子威赴武汉。经深入交流,三人达成共识:以湖北省建设厅名义,在汤池开办“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建设厅负责批文、经费与招生公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选派教员、招收学员,汤池合作社则提供场地与后勤保障。训练班虽以合作事业为名,实为培养抗日骨干,史称“汤池训练班”。
训练班于1937年12月18日正式开学,李范一任主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副书记陶铸任教务主任,父亲任总务主任。开学当日,陶铸即秘密建立党支部,并与父亲深夜长谈,要求父亲不公开党员身份与他单线联系,要求父亲与李先生保持良好关系,做好合作社的工作。陶铸敬重李范一,曾赋诗“寄怀李范一”,有“仰望高山不见峰”的诗句。李先生钦佩陶铸,他善书法,曾写“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此之谓大丈夫也”的条幅相赠。训练班虽由李范一挂名主持,实际灵魂与领导者为陶铸。初创时期,师生协力修缮破庙,以门板砖石为桌椅,稻草铺地为床,生活清苦却秩序井然。学员多数是流亡青年学生,少数是农民,同食同宿。课程涵盖政治理论、游击战术等,包括《党的建设》《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统一战线、农民运动等内容。父亲曾给学员授课,他用“旧瓶装新酒”的生动比喻,耐心说服部分不懂得借助合法名义开展革命斗争的学员,帮助他们转变思路。课余出演街头剧、宣传抗战思想,进行战斗演习、处处洋溢着蓬勃朝气。
然而,训练班自始便遭国民党顽固派频频干扰。父亲在回忆录中详述几段经历:
1938年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要员石毓灵突至汤池“视察”,他得知父亲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专业,私下利诱父亲,以高薪聘其出任随县农业技术学校校长。父亲一心抗日,婉拒其意。不久,有人举报李范一在汤池“训练共产党”。宋美龄立即遣特务头子康泽至汤池侦查。父亲迅即组织应对,并依李范一安排赴汉口“汇报”。在汉口,与国民党重要人物杨子福交谈了半天。父亲严正指出:李先生是辛亥革命老前辈、同盟会的老资格,与共产党合作,完全是出于国共团结抗战的初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抗日。李先生绝不会被他人利用或裹挟。这番话说得杨子福无言以对。此后,特务徐恩曾携费侠亦至汤池查探,却未获任何把柄,悻悻而去。
训练班在重重压力下坚持办学,共在汤池举办三期、武昌一期,培养学员六百余人。结业生部分赴延安或外省,多数留在湖北各县,以“合作事业指导员”身份设立办事处,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发动群众参与抗日,为后续组织抗日武装斗争奠定基础,直接推动了“应抗”游击武装的建立。汤池训练班成为发动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的摇篮,被誉为湖北的“小延安”;“汤池训练班”则被称作鄂中“小抗大”。李先念曾评价,“鄂豫边区三大战略支撑点”的建设,正是从汤池训练班起步的。在这里播下的抗战火种,最终在鄂中大地燃起了熊熊烈火。
也是在“汤池训练班”,父亲结识了母亲易齐萍。当时母亲在距汤池不远的京山县城参与抗日伤员救护工作,是一名抗日积极分子。
“应抗”崛起:从八条枪到四千雄师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军沿长江西进,应城危在旦夕,城里人心惶乱。陶铸、李范一等人撤离汤池后,我父亲意识到:动手的时机到了。他先是组织人员把合作社的重要设备和物资装船转移到湖区,接着从床底下取出不久前藏的二十四支驳壳枪和子弹,加上原本用来守护合作社的两支驳壳枪、一支勃朗宁手枪,总共凑了二十七支枪。随后,他找到了曾在旧军队任营长的共产党员鲁尔英。两人一拍即合,带领皂市米厂的员工,联合县保安大队詹中队长手下的十多人,共六十多人,正式打出“应城汤池抗日游击队”的旗号。这支队伍起初分为长枪队和短枪队:鲁尔英任短枪队队长,詹中队长则带领长枪队。他们在初冬的寒风冷雨中,顶着日军的炮火,一路辗转至京山丁家冲,与杨学诚、蔡松荣带领的一支仅十三人、八条枪的游击队汇合。不久,邓先柱又带来二十多名由矿工和农民组成的队伍,他们背着十几条捡来的枪加入进来;陈家河湖区抗日游击队的二十多人,也在郭仁泰、姜泽如的率领下前来会师。
1938年10月,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成立。一个月后,在陶铸、杨学诚等人的整合下,“应城抗日游击队”,也就是后来常被提起的“应抗”正式诞生。这支队伍就像磁铁一样,吸引了许多不甘做亡国奴的热血志士。应城县政府法官黄承香的侄子黄乐元,带着二十多人、二十多条枪找到我父亲,问他收不收。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只要是为了抗日,我们都欢迎!”随后,沈德纯、汪心一带领的湖区游击队,李又唐率领的应城县保安队,也陆续接受改编。还有曾在阎锡山部任职的容保民,也带着几条枪投奔而来。随着人员不断扩充,“应抗”整编为三个支队:徐休祥任第一支队长,李又唐任第二支队长,蔡松荣任第三支队长。当时,应城县县长孙耀华兼任司令,红军干部张文津担任参谋长,容保民任参谋处长,我父亲任副司令。从最初那“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不到两个月,“应抗”就发展为三个支队、七个中队,共计五百多人的武装。1939年10月,队伍更名为“应城县国民抗敌自卫总队”,我父亲出任总队长,支队也改为大队。到1940年,“应抗”已壮大至四千余人,并向新四军五师输送了大量兵员,补充到其三个主力团中。父亲常说,“应抗”是鄂中敌后战场上一面高扬的旗帜。每讲到这里,他总是情不自禁地小声吟诵:“神女没幽境,汤池流大川。独随朝宗水,赴海输微涓。”
筚路蓝缕:筑牢抗战根基
组织起抗日队伍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武器和经费问题。父亲在回忆录里详细记录了当时购买武器的过程。
1938年夏天,武汉保卫战打响,陶铸同志提议,李先生批准,父亲从汤池合作社的资金中提取了3600元,前往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请求协助购买枪支弹药。就在武汉沦陷的前几天,办事处传来好消息:枪支已从香港运抵。父亲立即带着合作社的年轻员工小马赶往汉口,从周恩来同志的警卫员龙飞虎同志手中,接过了24支德国造驳壳枪。他们将枪支和子弹分装在两个木箱里。父亲那时正值壮年,小马也是个结实的小伙子,两人各扛一个箱子,乘坐黄包车到竟陵旅社暂住,第二天一早就搭乘民船返回应城。回到汤池后,父亲把这两个木箱小心翼翼地藏在了自己睡觉的床底下。
随着抗日队伍不断壮大,物资供给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父亲又开始为筹集经费四处奔走。1939年7月,他们以应城县抗日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动员当地矿区和商界为“应抗”捐款。有一次,父亲和陶铸同志一同前往北乡张天道湾筹款。途中经过范家河时,远远望见日军士兵正在操练,还有几个妓女骑马在附近游荡。他们趁敌人不备,悄悄绕了过去。见到大矿主韩献廷后,父亲他们说明了来意,并商定召开一次矿主和商人的联席会议。与会的都是当地重要的实业家,包括韩诚记、陈愚安、陈伯惇、李季候、杨友吾等。父亲和陶铸同志向他们强调:“抗日救亡,人人有责。”矿商们虽然纷纷表示愿意捐款,但也道出了难处:日军经常强迫他们交钱,伪军、土匪和其他顽固势力也时常到矿区勒索。他们希望“应抗”能够肃清这些乱象。陶铸同志当即郑重承诺:“我们建立抗日队伍,就是为了打击鬼子和汉奸!”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在场的矿商,他们当场就捐出了上万元现金,并承诺此后每月都会继续捐款,金额从四万五千到十二万元不等。这些枪支和经费,为“应抗”队伍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烽火硝烟:四场经典战斗
在我父亲留下的回忆录里,记载着许多鄂豫边区抗战时期的往事。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其中四个,“应抗”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日的故事。
公安寨伏击战
1939年春天,鄂中的日军气焰嚣张,经常沿着富水河运输物资。我们的情报网络准确获知:3月底将有一支日军船队经过公安寨河段下行,船上载有百余名日军和一个所谓的“慰问团”,护航兵力约一个中队。父亲他们决定在此设伏。这是“应抗”成立以来的第一场大仗,陶铸亲自带队,从共产党员较
多、战斗力较强的蔡松荣、黄定陆支队中挑选了160多名队员。趁着夜色,部队秘密抵达公安寨。这里地势险要,临河处峭壁高耸,富水河在此拐弯,水流湍急,是打伏击的理想地点。陶铸令蔡松荣、黄定陆担任一线指挥,战士们携带轻机枪、步枪等武器,埋伏在右岸山坡,形成了居高临下的有利态势。3月30日清晨,日军的船队缓缓驶入伏击圈。一声令下,机枪、步枪骤然开火,密集的火力封锁了河道。掷弹手们将手榴弹精准地投向敌船,其中载着“慰问团”的船只被迫搁浅。“应抗”的勇士们如猛虎般扑上搁浅的敌船,消灭敌人、收缴武器,动作干净利落,完成后迅速撤离。日军虽然拼死抵抗,但因地形不利,难以组织有效反击。战斗持续到中午,击毙日军二十余人,其中包括一名皇族亲王,他正是“劳军团”的团长。此战缴获了步枪、轻机枪、掷弹筒及一批军需物资,“应抗”仅牺牲四人,以极小代价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场战斗规模虽不大,却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日热情,也让“应抗”声名远扬。
夜袭云梦城
1939年4月底,与应城相邻的云梦县城,城南墙体有一处被炸开的缺口。当时城内日军只有一个宣抚班和伪军驻守。“应抗”果断决定:夜袭云梦县城。4月30日晚,陶铸率领四百多名游击队员秘密出动。部队绕过官渡口,在午夜前抵达城西,随后兵分两路:一部在外围警戒打援,主力则由支队长徐休祥、蔡松荣率领,直扑城南缺口。尖兵像暗影般悄无声息地越过缺口,迅速控制了城楼并打开城门。大队人马涌入沉睡的城中,直扑日伪军盘踞的天后宫大庙。战斗瞬间打响。我军行动迅猛,在各个据点消灭敌人,很快救出了被关押的百姓。一股日军凭借房舍和机枪负隅顽抗。在强攻不利的情况下,指挥员果断采用火攻。熊熊烈焰卷起,顽敌葬身火海。激战持续到拂晓,游击队员点燃了敌军弹药库,震天动地的爆炸声中,部队从容撤离,带着战利品和获救群众消失在晨雾中。这次战斗击毙敌军二十余人,俘虏三十多人,缴获枪支二十余支、子弹万余发,还焚毁了敌军的重要物资。云梦夜袭战,成为鄂豫边区首次攻克日占县城的成功战例。
马家冲突围负伤
1939年12月的一天,上级通知父亲去京山马家冲参加会议,随行的只有两名警卫员。次日拂晓,日军的枪声突然划破晨雾,他们被包围了。父亲立即组织突围,却在山坡上与日军正面遭遇。敌人的机枪疯狂扫射,警卫员小杨牺牲,警卫员许贵喜负重伤。父亲从血泊中拾起小杨的驳壳枪和望远镜,带领剩余人员且战且退。撤回马家冲时,父亲才发觉右腿不听使唤。低头看去,裤腿已被鲜血浸透。卫生员紧急为他处理伤口时,父亲心心念念的却是必须尽快回到“应抗”总队指挥战斗。夜幕降临时,父亲强忍伤痛,骑着缴获的日军战马带队突围。同行的《七七报》主编李苍江同志,在穿越宋应公路渡河时,为掩护大家不幸牺牲。望着战友倒下的身影,父亲咬紧牙关继续前行,最终艰难抵达丁家冲根据地。母亲得知父亲负伤,连夜从驻地赶来照料。在母亲悉心照看下,父亲伤势稍有好转,便又投身到新的战斗中。
智取西湖岗
1940年早春二月,父亲的族侄许英豪走了近200多里路找到京山赵家冲见到我父亲。他痛诉日军在黄滩西湖岗设立据点,伪军队长周凤山带着三百余人横行乡里,不仅强行征粮、征物,更掳掠妇女,百姓苦不堪言。他恳求父亲带队伍去弄死那帮“狗汉奸”。还说父亲的另一个族侄许成,在周凤山手下当文书。许成对伪军的人员配置,枪支弹药存放的地点,守备情况、进出路线路都了如指掌。当时父亲身边只有一个警卫排,恰巧蔡松荣率领的队伍驻扎地离西湖岗不远。父亲立马带上警卫排去了蔡松荣的驻地,派许英豪叫来许成,进一步核实情况,许成表示愿意当内应。父亲决定当晚就行动。天黑后,父亲和蔡松荣带领300人的队伍让许英豪在前面带路直奔西湖岗。到伪军据点后,许英豪向许成发信号,许成悄悄打开据点大门。警卫排,先冲进去控制了岗哨,大队人马一涌而进。他们如神兵天降,还在睡梦中的伪军猝不及防,只得束手就擒。这场战斗未费一枪一弹,缴获重机枪六挺、长短枪三百余支、子弹数万发。蔡松荣特意挑选六支好枪送给警卫排,还将周凤山的坐骑赠予父亲。虽然狡诈的周凤山趁乱逃脱,但西湖岗的伪军据点就此拔除。
1940年1月,李先念任司令员领导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对鄂中的抗日游击队进行了整编,“应抗”徐休祥的第1大队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2团,徐休祥任团长,蔡松荣的3大队整编为挺进纵队第3团,蔡松荣任团长。1941年1月,豫鄂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第2团、第3团改编为第13旅第37团和39团,徐休祥、蔡松荣分别任团长。稍后,又从“应抗”中抽出一部分人马组成一个整编团,编入15旅。这三支劲旅在抗战烽火中不断成长,最终都成为新四军第五师的主力部队,为民族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应抗”这支地方武装,直到抗战胜利完成其历史使命。
为人民执政:建设豫鄂边区红色政权
1940年3月,在京山成立的"豫鄂边区宪政促进会",为建立边区民主政权铺路。陶铸同志担任主席,我父亲被调去担任他的副手。不久后陶铸同志调回延安,父亲便接下了主席的担子。从此,他投身于边区的民主政权建设。他带领大家一边发展游击战争,一边推进政权建设,还要组织工农业生产、搞活经济。他们推行减租减息,支援前线抗战,同时除奸惩霸、维持治安。因为这些实实在在的工作,老百姓都亲切地称他为"边区好主席"。1940年9月1日,边区党委在京山八字门召开第一次军政代表大会。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成立了鄂豫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父亲当选为办事处主任。1941年4月,这个机构改组为边区行政公署。在京山向家冲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父亲当选为行政公署主席,并在大会上代表行署作了工作报告。1942年3月,鄂豫边区第一届抗日人民代表大会在京山向家冲召开,126名代表出席。会议通过了《鄂豫边区施政纲领》,父亲再次当选行署主席。那一年格外艰难,边区既要应对日寇的"扫荡"和顽固派的"摩擦",又遭遇了严重的旱灾。但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行政公署带领大家克服困难,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果。1944年6月,边区召开第一次临时参议会,选举郑位三为议长,陈少敏,涂云庵为副议长。父亲继续当选行署主席,刘子厚为副主席。会议着重讨论了减租减息等关乎民生的重要议题。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到了10月,边区行政公署改为中原行政公署,父亲除了继续担任主席外,还兼任了江汉行署主席。行署机关也转移到了大悟县宣化店。
父亲在抗战烽火岁月的故事是敌后战场的一个缩影。父亲的抗战经历贯穿了从培训抗战骨干,发动群众、组建武装到建立红色政权的全过程,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如何以星火燎原之势,彻底粉碎了日寇“以战养战、以华治华”的战略阴谋。
这段历史警示我们:不可忘却日寇侵华之痛,更须铭记革命前辈在烽火中展现的勇气与智慧。正是千千万万如“应抗”战士般的普通民众,以血肉之躯筑起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用生命与信仰书写了民族解放的壮丽史诗。
(完)

1963年毛主席接见全国农业水
利科学规划会议大会代表
(左2为许子威)
1952年陪同李先念视察荆江分洪工程
(前排右1许子威、右2李先念)


父亲许子威,摄于1942年在鄂豫边区白果树湾


应城县国民抗敌自卫总队领导人:总队长许子威(右3)副总队
长王海山(右1)一支队队长徐休。(右2)摄于1939年秋
1942年鄂豫边区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边区参议会驻会委员与行署常务委员合影:许子威(2排右3)郑绍文(2排右2)陈少敏(3排右2)


父亲许子威与母亲易齐萍1985年摄于武汉住所
(整理:魏许思)
编辑:开门见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