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3年天,我在左联工作,周扬向我介绍了彭柏山。那时候他从洪湖出来,我安排他在左联工作。
当时上海左联有四个区:沪东、沪西、闸北和法南区(法租界和南市区)。我把他分配在法南区。区的负责人有周文、宋乐天等。
有一次,我上柏山家去,看他穷得没有饭吃,又没有钱,每天买几个烧饼,买两个铜板酱油,用大饼蘸着酱油吃,解决生活。我和他谈心,他很难过。那时候我的经济也困难,顶多给他一、两块钱,可以让他多活几天。我把这情况给鲁迅先生讲了,他嘱咐我在他老人家每月捐给左联的二十元钱中,拿几块钱给柏山,维持生活。有一次,我代鲁迅先生请左联的十来个青年作家吃饭,也请了柏山,他和鲁迅先生认识了。
左翼作家联盟,是以写作为主要战斗形式之一。柏山和我谈起,他看了《毁灭》,引起他强烈的创作欲望。因为他在湘鄂西苏区担任荆门、当阳、远安三个县的省委特派员,领导过武装斗争,接触了很多红军战士和干部,对这方面的生活有深刻的感受和印象。我竭力鼓励他写个中篇。他终于写成了一个短篇《崖边》。他拿给我看,这是一篇反映苏区人民斗争的作品,具有实际的斗争经验和生活内容。于是我把《崖边》介绍给杨骚,杨骚把它放在《作品》上,作为首篇发表了。接着,柏山继续写了《皮背心》、《忤逆》、《夜渡》和《枪》等短篇小说。
1934年冬天,听说他在街头被捕了。怎么被捕的?不了解。当时也听不到关于他的一点消息。过些时,又传说他被押到苏州去了。有一天,内山书店有一张明信片,寄给周豫才大人,署名陈友生。鲁迅先生要我看是谁写的?我看出是柏山的笔迹。我按照鲁迅先生的嘱咐复了信,信写得很简单。接着,就不断寄书、寄钱、寄衣服,还有两次寄过药品。凡是他生活上需要的东西,我尽量想法寄给他,直到他释放出狱。
1936年,我把他写的五篇短篇小说收集起来,交给当时巴金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结集出版。巴金正在办《文学丛刊》。这个集子题名《崖边》,因为《崖边》放在第一篇。由于柏山还在狱中,怕出书对他不利,我将柏山的原名冰山改为柏山了。
正在这时候,日本《改造社》的社长山本实彦到中国来,会见了鲁迅先生,要求中日两国"交换彼此的创作",作为艺术上进行交流的第一步,并请鲁迅先生尽推荐之责。鲁迅先生说:中国有两三个新进作家的作品,可以达到在《改造》杂志上刊登的水平,建议从扶植的目的予以刊载。鲁迅先生指出,“中国左翼作家是在锋刃之下写作的,稿费少得可怜。”鲁迅先生只选了萧军一人的作品,他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我。我选了周文、欧阳山……也选了柏山的《崖边》。并用日文在篇首写了他的简历:
"柏山,出生于湖南,姓彭。进过上海某大学,中途参加解放运动而退学。长期活动在 xxxx 区域,后回到上海。一边工作,一边创作。不幸的是,他和上面‘领导者’不合,要发表作品和批评都办不到。《崖边》也是在那种状态中写成的。好容易可以发表。又写了几个短篇。可是被南京政府逮捕,现在还不知呻吟在哪里的监狱中。因友人的编辑,六月中出版了短篇集《崖边》。
鲁迅先生目前卧病中,我代写了这个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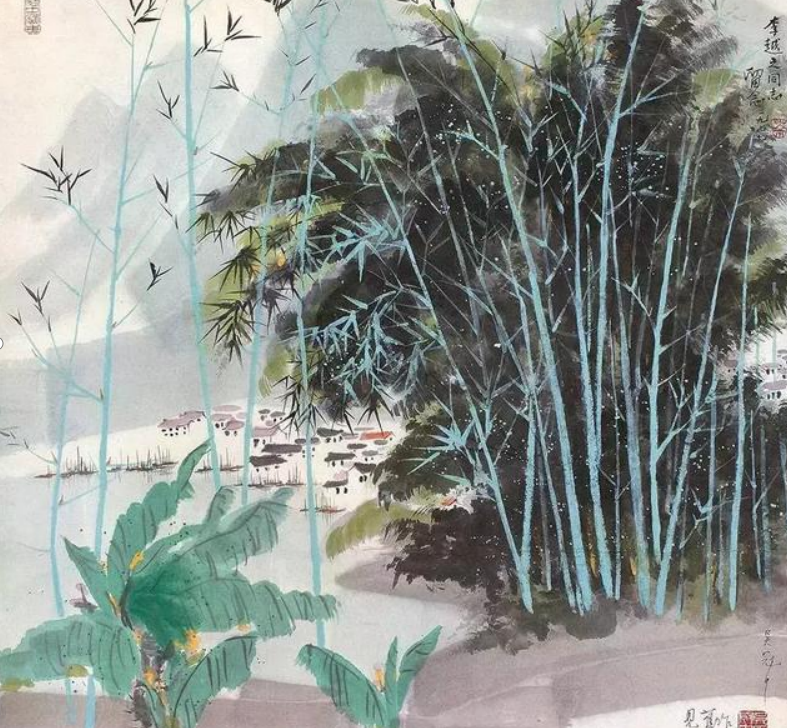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柏山被无条件释放出狱。我保存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1937年8月:13日:接柏山信。要寄几本书。
20日:乔峰留字,说柏山已来上海,约我明天和他见面。21日:去文化生活出版社会见柏山,未见到。出来在路上碰着了。同到冠生园吃茶,吃面。他读了很多书,经过了一些锻炼场面,正视现实的眼光和精神相当成长了……去耳耶处④。说是柏山可以住在他那里。下午送柏山到耳耶处。
1937年9月11日,是《七月》在上海创刊出版的日期,这是我自筹印费、编辑出版的。开始是旬刊。在第2期上,就刊有柏山的小说《苏州一炸弹》。可是办到第3期,没有钱买纸张,人力也不够,于是决定迁武汉。10月19日,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七月》出了纪念专辑。柏山寄来了《活的依旧在斗争》的悼文。这篇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使我很感动。柏山去皖南新四军后,都是反映部队生活的。
1940年春天,他去敌后工作,我辗转重庆、香港等地,整整有十年不知他的音讯。1949年我从东北到北平,我们才联系上了。
1950年1月里,我从北京回上海,路过徐州。这是他所在的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四军军部的驻地,我们欣然重逢了。
柏山和我谈起,在野战军多年,都是参加大兵团作战,进行攻坚战、运动战。部队和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生死的搏斗。特别在豫东战役、淮海战役中,部队高度的自觉性,令人惊叹!部队英勇牺牲的气概,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为历史上所罕见。他很激动,决心写一部长篇小说,纪念这些为祖国为人民牺牲的英雄。他跟我谈了写作的设想。他说:“革命的文学家,必须和革命共着命运,必须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跳动。”当时他已经拟了初步的写作提纲,定名为《胜利者》(即《战争与人民》),他征求我的意见。
队生活我完全不了解。我向他提出,在勾勒、描写人物的时候,每个人在每个场合的感情如何起伏、变化、发展,都要合乎生活的逻辑。这是我设身处地的想法。他接受了我的意见,也增加我的自信。当时,我只向他提了这一点意见。后来,我们继续通信,几乎都是谈创作的问题。有时,他把初稿寄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我认真地谈我的看法并复信给他。
时间消逝得很快,我和他都在不幸的情况下,度过了漫长的坎坷而艰辛的岁月。前年秋天,《战争与人民》终于出版了。当我掀开扉页,看见他的手迹,看到他坐在桌前读书的身影,我久久地凝视着,心里涌上了无限惆怅的怀念。我能说什么呢?
编辑:岁月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