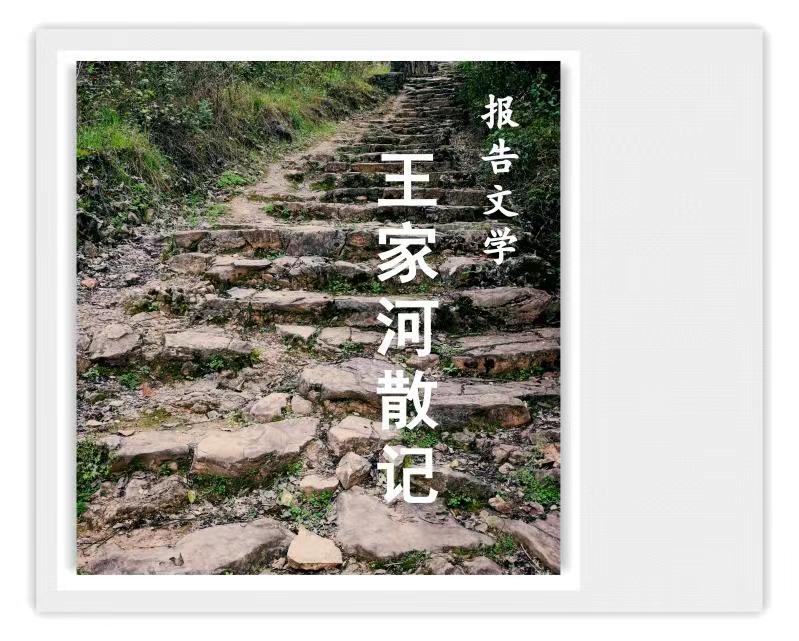铁道兵文苑
【原创】报告文学《王家河散记》连载8
十六
第二天傍晚,学校里响起一阵鞭炮声,我赶着去看热闹。只见校门口站着许多人说说笑笑。拨开人群,学校里边的确热闹,鞭炮声合着孩子们敲碗的叮当声,灶房门前排起了两行长队,前面的你推我挤,后面的不停呐喊:“吃饭喽,吃饭喽……”老师们全都出来维持秩序,大声招呼着:“同学们,不要挤,先让一二年级和学前班的小弟弟小妹妹打饭好不好”。李校长在攒动的人群中看见我,我也看见他,我指着这场面说:“学校今个真热闹呀!” 李校长兴高采烈地合不拢嘴:“热闹么,这比咱农村谁家过事还热闹”。我把他拉到一边,问:“昨晚上那个娃不要紧吧?”“没事,这还让你费心了。俺一去,大夫给挂了一瓶点滴,烧立马就退了,拐枣儿这娃太小,才上学前班,自己照料不了自己,咱就得多操些心,天亮时,娃就跟我回来了,你看……” 顺着李校长手指的方向,只见拐枣儿从队伍中钻出来,一手端着菜碗 ,一手用筷子头串着一个热腾腾的蒸馍,嘴上还噙了一沓子饭票。
事隔两天,我在班车上遇到了李校长和包村干部赵党峰。那天,车上的人特别多,走道上堆了好几袋核桃,听乘客讲,今个县上过会。李校长起身腾了一个位子给我,便顺势坐在我身边的核桃袋子上,我扭过头,向党峰招了招手:“你到县上去?”他拍了一下脚下的袋子,说:“回一趟部队,给战友们带了些核桃,让大伙尝个鲜。你呢?”“我回西安开会。”话音未落,只听见司机老贾给他卖票的媳妇喊:“车门关好,走!” 车很重,摇摇晃晃,走得很慢。
这里的村民不太讲究,在车厢里吸烟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清晨的阳光从车窗玻璃泻进来,耀眼的光线里,翻滚的烟雾混合着颠起的灰尘显得格外清晰。有个抱小孩的妇女,把孩子的脸塞进自己的怀里,然后打开车窗,面向车外,任风呼呼地吹着。二十多里的乡间路走了近两个小时,终于爬上了国道。
车不再颠簸了,我这才和李校长聊了起来。他说,这次进城一是到教育局催要经费,询问教师等级培训情况和补发几年前拖欠教师工资的事;二来买点东西回去,庆祝教师节,我不知道山区小学是如何过教师节,一听到教师节三个字,感到挺温馨,因为这是学校里最最隆重的盛典。可是,当我了解到这个学校的教师节只是割五斤肉,全校师生大会餐,给每位老师两盒“金丝猴”香烟,心里一阵子翻腾,我想哭,我不敢再看李校长。
下车后,我没有回家,端直去了西安市第七十中学。七十中校园处处洋溢着喜气,一条大红横幅映入眼帘:“热烈庆祝第七十中学建校四十周年暨二十一届教师节”。教学楼前布满了鲜花和彩旗,鼓号队的同学在紧张地排练着“欢迎曲”,操场上摆放着许多单位送来的贺词、字画、镜框、花瓶,与双店子中心小学的惜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无心仔细去看,绕过教学楼,直接走进了校长沈芝伟的办公室。沈校长是教育界的巾帼英雄,今年五一,又荣获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我们好多年前就认识,她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老大姐。沈校长今天格外喜兴,穿着一身粉红色的西服套裙,她一抬头,诧异地说:“哎呀!你咋来了?”
“大姐不欢迎?”我急忙走上前握住她的手。
“你是稀客,没有事不来我这里,该不是来检查教育收费吧。”沈校长跟我开玩笑地说。
“哎!沈校长,您这回说错了,我今天来,是到您的门前化缘来了。”
沈校长给我沏了一杯茶,说:“看看看,我说你有事,没错吧,是这,我这儿正在筹备明天的庆祝活动,事情多得很,对不起,咱长话短说。” 沈校长确实忙,胖胖的脸庞通红,刘海儿下渗出的汗珠都顾不上擦。
我赶紧把山区学校的困难情况给沈校长简单地讲了一下,希望他们能帮扶一把,她听完后,心情也显得有些沉重,略顿了一会,说:“你是我们教育系统外的人,都在为教育上的事奔走,我更有责任帮助。你说,捐钱还是捐物?” 沈校长爽快地问我。
“钱!”
“多少?”
“您看情况。”
“两千元行不?”
“行得很。”我真的喜出望外,我想,山区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听到这个消息该多么高兴呀!我当即就给李校长通了电话,电话那边李校长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十七
第二天,我应邀参加了七十中学的校庆,与学校的教职员工共进午餐。席间,我斟了满满一杯酒,走到沈校长面前:“沈大姐,我代表双庙子中心小学的师生敬您一杯。”话音未落,她身边的一位领导站起来问我:“你是双庙子小学的?”
“不是,我是……”我刚要回答,沈校长赶忙介绍:“他是咱们物价局的同志。”然后又指着那位领导说:“这是咱们市政协的李广瑞李主席”。李主席听说我在山区搞扶贫帮建,深情地说:“王家河乡在大山深处,九个自然村都分布在山梁梁上,老百姓的生活艰苦得很,我去过好多次,现在也不知道那里的情况咋样了。”
“那个地方您去过?”他怎么到过那个小地方,我有些不相信。
“嗨,二十年前,我就在周至县当县委书记,无论平原山区,什么地方我没去过,那个时候有近30个乡镇,我都跑过。后来到了市教育局,又到了市政协,县上去的也就少了。”李主席用手指在桌上轻轻地弹着,从他的表情上看得出,是在回忆二十年前的那一段生活。
我给李主席讲了那里的变化,也讲了当地的教育现状,特别提到师资缺乏和教师待遇太低的问题,请领导在政协会上呼吁。李主席没等我讲完就说:“不用说了,这些情况我知道。现在我们整天讲再穷不能穷教育,但是我们一些地方领导同志对教育事业不重视,只知道抓企业。教育是公共事业,费钱劳人还不见成绩,办企业,见效益,显政绩,一举两得,他们何乐不为?”李主席越说越激动:“我们把教育抓不好,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住子孙后代呀!”
听到这些,我的心灵深处受到重重地撞击,从我国古代教育开山鼻祖孔子首创讲学风气,主张‘有教无类’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开始,沿袭了两千多年封建文化教育,出现了许多蜚声中外、叹为观止的教育家,尽管说有着‘惟有读书高’的极大政治功利,但同时也为传承中国教育,弘扬文化品行,激发民族精神起到莫大的推进作用,他们无不崇尚教育,把教育推向了极致。而今天,面对着世界经济的挑战,面对着加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亟需一大批高素质的科技精英,我们必须着力于教育事业、着意于提高素质、着眼于中华腾飞,文化教育已成为发展的基石,这是全民族、全社会的共识。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然而,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还很不均衡,特别是我们西部地区的农村,教育还很落后,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我们神圣的职责。我们共产党人难道不如封建社会的文人墨客?是致力于教育这个千秋大业,还是漠视教育,垂青个人政绩,这是两种判然殊同的价值取向,更是政治走向。
“来,我为我们七十中四十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也为关心我们教育事业的各位朋友的健康,咱们干杯!”李主席说完,举杯一饮而尽。
几天之后,双庙子中心小学的李校长特意制作了一面写着“帮困助学,功在千秋”的锦旗,让我领他去了市七十中,还顺便带了一点当地的土特产核桃和自家产的猕猴桃。走到学校门口时一再问我:“这东西不值钱,是不是太小气了?”山里的人就是厚道。
“有这些心意就足够了,你还想拉一卡车不行?”听了这话,李校长一声不吭,只是憨憨地笑着。
令人想象不到的是,临走时,他还带回了七十中学师生给他们学校捐赠的一百多件过冬的衣物。
十八
在离王家河乡政府驻地几十里的玉皇庙村,有一个国家级的金丝猴野生动物保护区,好多人都以为是金丝猴观赏旅游景点。我听说西北大学有位叫李保国的教授,带领几名研究人员,在那里默默地工作了十多年,为了考察研究金丝猴的生活习性、繁衍和生态环境,和动物零距离朝夕相处,工作环境相当困难,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可这里通透着一种献身科学的精神,凸显着一种勇于探索的态度,令人感动和钦佩。我曾经在一本厚厚的杂志上,看到过对这里的报道,但与当地百姓的讲述和评价,这则报道显得黯然。我设想利用国庆节长假进去一次,看看那里的人,看看那里的山,只可惜,一场罕见的洪水泡汤了我的计划。
这场洪水来得太猛,据说是五十年来罕见的一次。电视新闻报道,肆虐的洪水完全吞没了王家河境内的乡间大路,冲上了国道,山体滑坡,道路坍塌,桥梁断裂,全线封闭,进山的车辆排成了几里路的长龙。看着让人心魄震颤、翻卷呼啸的巨浪,由不得使我惦记起双庙子小学的孩子,他们撤离了吗?新修的人畜饮水工程现在怎么样了?还有在金丝猴动物保护区的同志……
天一放晴,乡上赵书记就把电话打了过来,焦急地讲,乡间大路基本上全毁了,他是翻山越岭,沿着小路徒步走出来的。又说,下一步就是到县上争取救灾资金,动员群众修复道路。
灾后的二十多天,我按照领导的指示,奔波在好多部门,一直设法筹集救灾资金,先后筹到维修蓄水池资金五千元和小学校舍修缮资金一千元。他们多么需要这些钱呀!我想象中王家河的修路工地上,车水马龙,乡上领导正在带领着群众,热火朝天地开展自救。然而,大失所望,除了一名乡上领导带了两个干部在乡政府院子职守外,其余的人基本上放假了,当地的群众也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儿最着急的是小学的李校长和供销社的纪村长,一个急于到县上给学生磨面买菜;一个急于到县上为村民的秋播采购化肥。有的群众讲了,路修好了我们能咋,还不是给干部们修的,他们的小卧车跑来跑去,能给群众办多少事?有个班车吧,同样是人,价钱不一样,从乡上到县城,村民掏十块,乡政府干部才是七块,凭啥,干部和咱隔层层着呢!这些话虽然看上去有些消极,但是又颇有道理,它说明了一个浅显又深刻的问题,我们的部分干部和群众离心离德了。
记得最后一次去王家河乡是2018年秋,乡间大路基本通了,有些路段准备改道,筑路的技术人员攀缘在陡峭石壁上,架着水平仪进行测量,清脆的哨声划破寂静的山林,小红旗在一片翠绿的衬托下摆动,格外耀眼。车走了一段,又看到一根根水泥电杆树起来了,新挂的电线舒展地伸向远方,几只喜鹊在电杆头翘起尾巴跳着、叫着。
这一天正赶上庙会,群众举着红红绿绿的纸幡,敲锣打鼓,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街上,我趁着热闹凑到跟前,想看看这儿怎么赶庙会,一位白发银须的老者,手里攥着刚从大伙儿那里收起的香火钱,对我说:“赶庙会就是大家过一会要到对面山坡的庙里去烧香拜佛,完事以后,顺便采买点东西。”
“烧香拜佛总得有个念想吧?”我有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意思。
拥挤昏暗的庙堂里,匍匐着好多人,一把香火高高地举着,嘴里喃喃地念着:
“俺保佑在河南煤矿上干活的老汉平平安安”。
“我保佑俺的娃们在山外头学习进步”。
“我保佑俺儿媳妇明年给咱生个带把儿的”。
“咱保佑明年有一个好收成”。
是祈祷?更是慰藉,是释怀?更是向往。这里的老百姓把现实的委屈和未来的渴望,盛满这天地之间,把豁达的心态和浑朴的情怀溶进这山水之中。
王家河呀王家河,每当我看到它的时候,百感交集。王家河的人,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深处,面对着群山峻岭,显得是那样的渺小,这里森林茂密,却无人砍伐,过着留有青山在,只能拾柴禾的日子,拳头里攥着无奈;这里矿产资源丰富,却无人开采,金碗里装着尴尬,他们也有过梦想,也懂得什么是财富,什么是滋润,因为他们曾经见过,可今天怎么啦?同样是面对着群山峻岭,王家河的人,又显得是那样的崇高,他们更懂得王家河是黑河的上游,这里的生态环境需要保护。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利益,宁愿终年厮守着清贫,也要呵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守望着这条日夜奔腾不息的清流,这条牵系着西安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生命河……(未完待续)

本人爱好写作和摄影,多篇散文在《长安瞭望》、《秦川文化》、《西安旧事》以及网络杂志发表,多幅摄影作品在影展获奖。
(本版编辑: 老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