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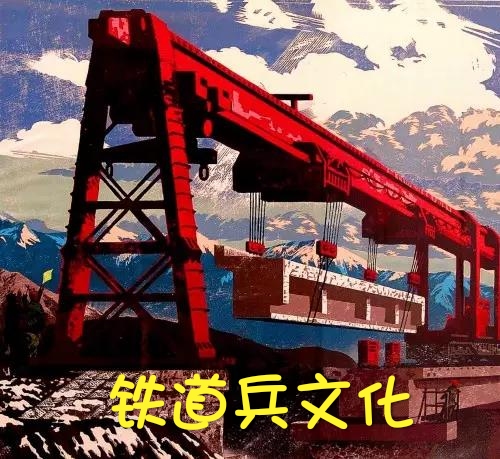
荐读‖《铁血雄师·我见到了毛主席》
梅梓祥导读:
我们在过去的纪录片以及现在的网络视频中,看到过领袖接见各种人:领袖或招手,或鼓掌,面向人群走过;有时候与其他陪同的领导就坐,与被接见者合影留念。但“接见”的背后情景,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
徐殿勋写的《我见到了毛主席》一文,介绍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全过程:入睡后被通知到北京;连夜冒雪驱车十几个小时,在规定的时间到达北京指定地点,获知被毛主席接见,中断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几日后,紧急集合,赶往北京体育馆;毛主席等领导出现在主席台,“毛主席万岁!”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深感是个人的光荣,更是援越抗美部队的光荣。
细节耐人寻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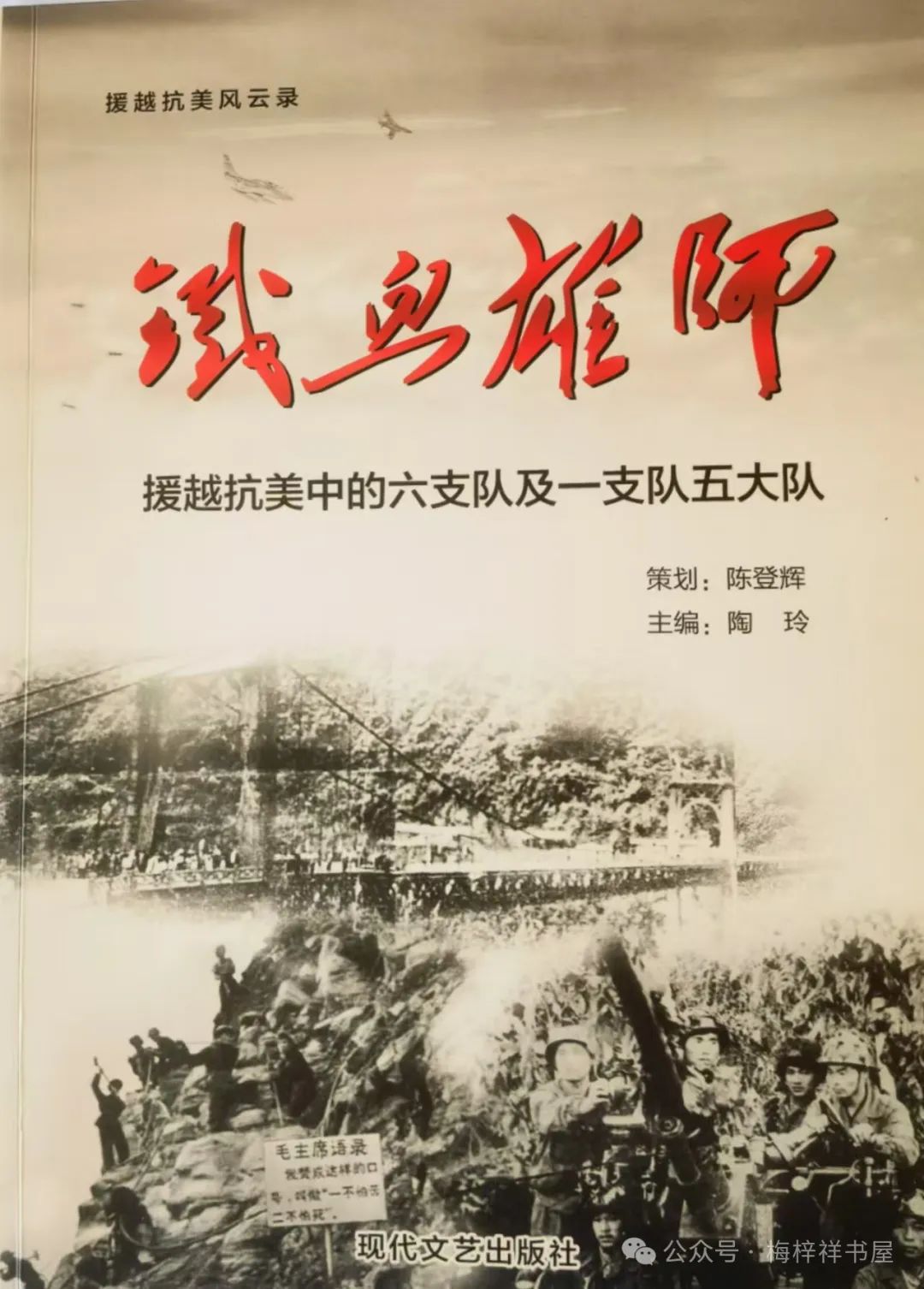
我见到了毛主席
六支队(13师) 徐殿勋
援越抗美结束后,我们部队从炎热潮湿的亚热带丛林里奉命调回到了山西的塞外高原,参加京原铁路建设。这种突然的巨大气候环境反差,对很多人来说,都不能适应,特别是从来没有到过北方的江南人,真是巨大的考验。塞外的黄土高原,真是“山高不长草,风刮黄沙跑,吃水贵如油,四季难洗澡。”不少人脸上一层一层地起皮,口干舌燥,经过长时间以后才慢慢缓解。
大概是在1969年的元月五六号,晚上十点多钟,我们已经入睡了,突然通信员敲门让我们赶快起床,穿上皮袄和大头鞋,带上牙具准备出发。我们问他去哪里?通信员说:“可能是去北京。”
这个时候大同去北京的火车已经没有了,而北京要求我们师、团干部在第二天中午的12点之前必须赶到。当时正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组织了7辆北京牌212吉普车,每辆车上都配备了两名司机,冒雪连夜赶往北京。由于当天雪下的很大,又是晚上,一路十分艰难。沿着狭窄的沙石路,穿越太行山十八盘险境,从紫荆关长城古道进入京大(名府)国道。经过一夜的奔波,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我们到达河北的高碑店,在兄弟部队吃了早饭后,又继续出发直奔北京。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连续奔波,我们终于在规定时间之前到达了目的地,并在招待所安顿下来。一进入招待所,上级就规定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不准写信,总之中断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我们只能在住处等待。
这时候,大家已经知道是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了。到了元月8日早上,突然响起紧急集合哨声,我们立刻赶往北京体育馆。当我们进入会场的时候,陆、海、空三军的待接见人员,已经陆续入场。我们被安排在最佳位置,估计是因为我们刚从援越抗美战场回来的缘故吧。
会场内,看到军委办事组的人员都在台上来回走动,各军区的领导也已经排队站在了台上。突然间,我看到了我在当步兵时的师长徐国贤,我们面带微笑地互相招手致意。能和老首长一起受阅,更使我感到十分荣幸!
受阅台上,各军、兵种方队人员都显得特别兴奋和激动。当毛主席和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出现在接见台上时,全场顿时高声响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刚开始,毛主席主要是面向台下招手,此时安排在接见台侧面的海军方队人员,因为看不到毛主席,突然都站了起来。周恩来总理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情况,招手示意大家坐好,随后走到了毛主席跟前,扶着毛主席和海军方队见面招手。
这就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驻京部队各军、兵种团以上干部的难忘情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能受到毛主席接见,这必定与我们刚从援越抗美战场回来有关。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光荣,也是战友们的光荣,更是我们援越抗美部队的光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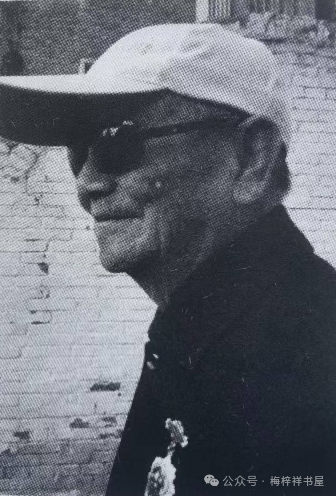
作者简介:徐殿勋,山西人,1932年出生,1946年8月14岁就参加吕梁军区警卫队,接着就跨过黄河,参加延安保卫战和整个大西北的解放。1950年调入空军航校,1951年8月调入空军17师任军械员、军械组长、军械副主任、主任、机务大队副大队长、基地训练科副科长,组织计划科科长。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1965年调入铁道兵,任13师后勤部营房科长,同年底参加援越抗美。1976年转业到康城电厂,任副厂长、厂长、党委副书记。1994年6月离休。
编辑:开门见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