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忆“官兵互教”》
作者:杨振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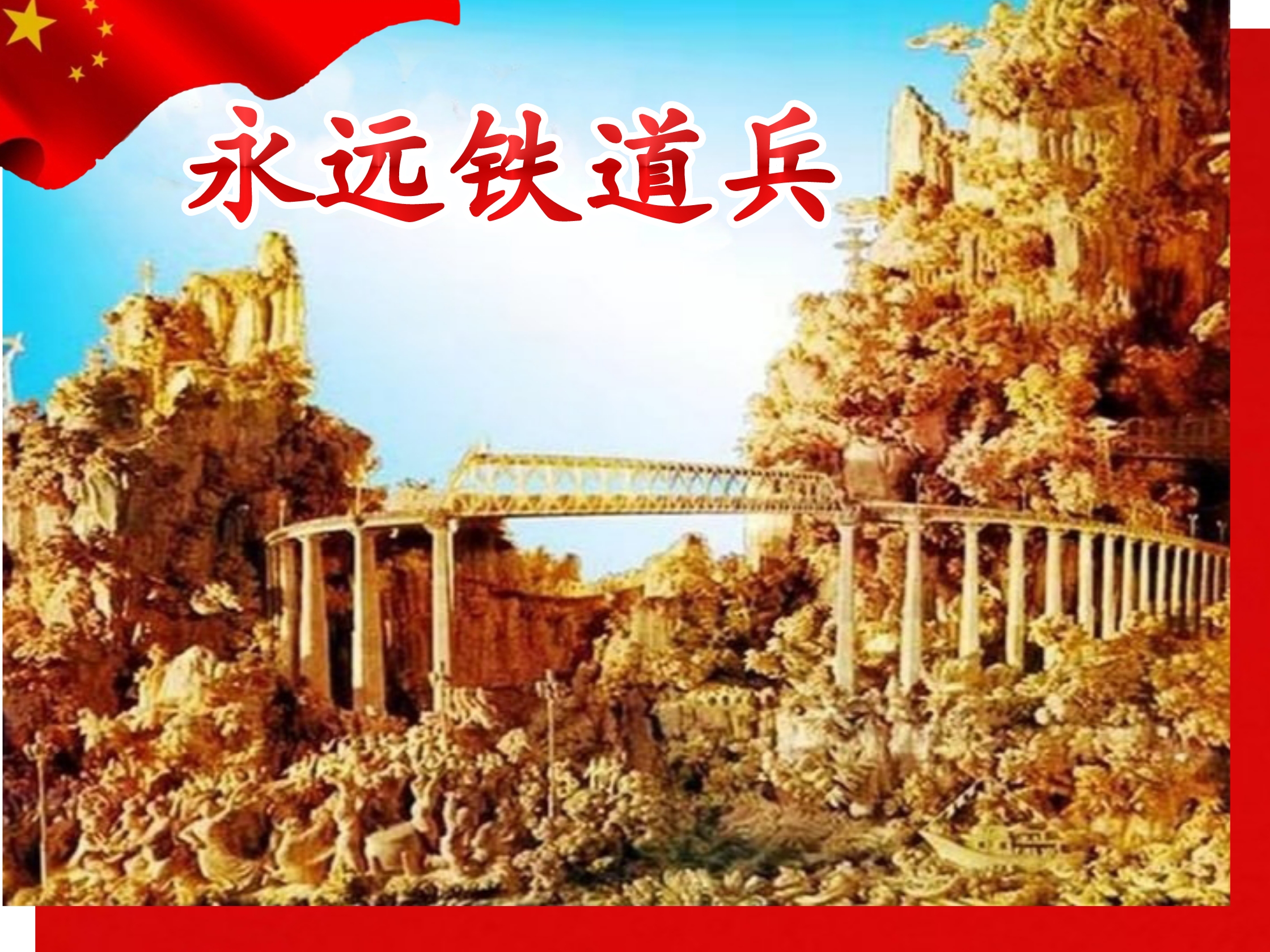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大多请一位专家学者讲解一个主题,我衷心赞美这一制度。回忆军旅生涯中“官兵互教、教学相长”和家中的“长幼互学”的情景,特别是其中的“兵教官”和“长学幼”的情景,感悟颇深:
军营我是一个兵,
班排连长是上峰。
官的职责管教兵,
我军士兵当先生。
集体学习兵讲课,
官坐台下认真听。注1
将帅首学原子弹,
教官就是一书生。注2
官兵互教兴军校,
教学质量大提升。注3
九岁我去扫盲班,
长辈忙把老师称。注4
如今常向孙请教,
白发翁妪当学生。注5
学习不分辈大小,
更不计较官与兵。
互教互学共进步,
庚续华夏好传统。
注1: 我当兵时,无论学政治、学文化,还是学军事,都提倡“官兵互教”(即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我是兵,也曾被聘为“教官”为大家上课,即“兵教兵”;有时还专门为干部讲课,即“兵教官”;特别是每周一次的连、排“民主生活会”,开展政治军事生活“三大民主”,战士们都踊跃发言提意见,指名道姓地批评干部,实为“兵教官”、“兵管官”的民主监督制度,非常好!
注2: 五十年代,我军组织将帅们首次学习原子弹知识,上课的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年轻老师李儒哲(是典型的“兵教官”)。李老师是河北省新乐县人,和我是近同乡。他以全省状元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后,留校搞原子弹研究,六十年代调到核实验基地工作,八十年代选调到我们石家庄铁道兵学院任教。与我同事多年,已病逝。
注3: 我们石家庄铁道兵学院(现铁道大学的前身)非常提倡“官兵互教、教学相长”,即经常请有实践经验的学员上讲台給大家(包括教官)讲案例、传技艺,实行“兵教兵、兵教官”,促进了教学质量,经常受到上级表彰和媒体报道。
注4:解放后,党和政府发起“扫除文盲运动”,毛主席亲自給警卫战士上课、批改作业!我八九岁时才读一两年书,就在“扫盲班”当“小先生”(老师),在地窨子里、树荫下、水井旁、地头边“见缝插针”地教叔婶等长辈们识字。至今还有长辈说,我会写名字是你教的,你是“老师”。
注5: 我们家有“互教互学”的学习风气。我既给儿孙忆家史、讲传统,又虚心向他们请教新知识。特别是孙子孙女见面常常主动问:“电脑、手机有什么问题?我包教包会!”让我心里暖融融的。
(2023.2.25)160

编辑:向日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