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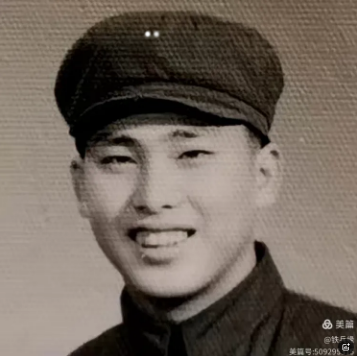
铁道兵10师49团汽车连,是我在襄渝铁路建设时期待得最久的地方。汽车连的部队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5849部队59分队。我对这里有着难以言喻的情感。可惜那时没有手机,照相机也极少,否则定能记录下许多珍贵的记忆。

1971年3月,我刚满十八岁,来到了汽车连。到连后,我们的作息完全听从军号指令,直到现在,我仍能分辨出军号的种类。早上六点,起床号响起,我们迅速起身;紧接着出操号吹响,大家集合出操。出操地点一般就在车场,内容多为队列训练或跑步等体能训练。出操后有30分钟时间洗漱、整理内务:被子要叠成“豆腐块”,枪支、牙缸牙刷、脸盆等物品都需摆放整齐(这项工作有时会进行检查评比)。早上七点吃早饭,各班拿着铝盆、铝桶到炊事班打饭——铝盆盛菜,铝桶盛饭。打饭没有特殊规定,全凭自觉,班里几乎每位战友都主动承担过打饭任务。
早上八点,军号一响,我们准时到车间工作。我们修理排的大车间十分气派,中间区域用于修车,两侧分布着搪缸、电工、焊工等小工作室,车间还有二层,我们有时会偷偷爬上去玩耍。修理车间的大部分空间都被我们十五班(大修班)占用。
下午六点吃晚饭,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有时还会进行晚点名,简单总结当天工作、布置次日任务。我记得喻政治指导员常常负责晚点名讲话。有一次晚点名,喻指导员批评了驾驶排的一名战士:有位老乡想搭他的车,他没同意,这位女老乡便爬到车厢上不肯下来。这位战友急了,爬上车厢把女老乡硬抱了下来,还说着“你跟老子下来”。指导员严肃批评道:“这是什么影响?知道的是你不让她搭顺风车,不知道的还以为光天化日之下解放军欺负大姑娘,成何体统!”这个情节我至今记忆深刻,不知驾驶排的战友们是否还有印象,也不知这位战友是否在咱们的群里。
晚上十点,熄灯号响起,我们准时熄灯休息。当然,有时半夜会有紧急集合——紧急集合以哨声为令,要求打背包、全副武装,且不允许开灯。我记得在汽车连第一次紧急集合时,抹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背包带,便用手电闪了一下。班长立刻喝问“谁”,就在这一瞬间,我看到了背包带,赶紧打好背包,迅速归队集合。部队对作息要求严格,目的是让战士们养成良好的时间观念,更好地适应军营生活。

在49团汽车连,我们修理排和驾驶排的关系十分亲密。襄渝铁路建设鼎盛时期,汽车连共有113台车,修理任务极为繁重。我们修理的车型包括CA10型大解放车、翻斗车、嘎斯51,有时团里的小车也会送到汽车连维修。我记得团里有位开北京吉普的四川兵,大概是1965年入伍的,圆脸白肤、大眼睛,长得很帅气,好像姓金,具体姓氏记不太清了。汽车连的战友们常开玩笑说,驾驶排和修理排的关系是“一人一半爷”:车子进了修理车间,修理排就是“爷”;车子上了路,驾驶排就是“爷”。我和驾驶排打交道不多,主要是修车或搭顺风车,不过也有例外。比如驾驶排的陈树建战友,他是1971年入伍的四川达州兵,每次执行完任务回连后,一有空就爱找我们班的刘军驰玩耍。他俩是同年入伍的四川“娃娃兵”,一来二去,我们也都熟悉了。据树建战友说,在襄渝线上,驾驶排的任务同样繁重:每天要从吕河往返西安,四天一个来回,非常辛苦,一年到头基本没有休息时间。他们班有八台新车(具体是哪个班我记不清了),主要负责运输高架、钢管、轻轨等物资,这些东西都极难装载运输。从西安出发,翻越秦岭,经过月河梁、平河梁,到达宁陕时天就黑了;第二天吃过早饭继续出发,经石泉、汉阴抵达安康,再把物资送到施工连队,等卸完货返回汽车连时,往往已经很晚了。如果车辆没有大毛病,第二天吃过早饭、加完油,就又要出发前往西安。我觉得他们的辛苦程度,丝毫不亚于我们修理排。我还记得有一次从西安回汽车连,坐的是咱们连的顺风车,可能是重车,拉的什么物资已经记不清了。车子从秦岭分水岭下来,快到沙沟时,后轮突然响了一声,随后便无法移动。我下车查看,发现汽车后轮半轴断了。当时正值下山,我提议把半轴抽出来,空车滑行下山。可半轴一抽,刹车就失效了,风险极大。我们只好一人握方向盘,一人负责拉手刹,同时紧盯车外以防突发情况。就这样,大家神经紧绷地将车安全滑到沙沟,心里才松了口气。到沙沟后,我们立刻联系汽车连,让他们派小修班带着配件前来救援。这是我在汽车连亲身经历的一件惊心动魄的事。

我还记得有一次团里放电影,我因故没去,一个人在连队里闲逛,突然遇到了曹连长。曹连长操着一口地道的山东话叫住我:“小铁,你嫂子来了,带了山东煎饼,快过去吃点!”我说刚吃过饭,不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连长夫人——我的山东嫂子。嫂子为人朴实,还带着个孩子,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群里的冬梅或红梅。转眼几十年过去,孩子都已成了大姑娘,我也认不出了。今年年初,淄博的曹建国战友给我看了曹连长家的全家福,我对嫂子还有些印象。前不久,我和家人开车从郑州去济南,路过山东菏泽曹县时,不由得又想起了我的老连长。曹云德连长是1958年入伍的山东曹县兵,在部队时对我非常好,是我敬重的连首长之一,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愿他在天堂没有病痛,一切安好。听战友们说,喻指导员转业后的情况不太好,可惜我们离开部队后失去了联系,没能帮上他什么忙,心里至今仍有些遗憾。
在连首长中,除了连长和指导员,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杜玉良连长。我在汽车连时,他是副连长。杜连长经常到我们修理排来,听说他曾经当过修理排长,对修理排很有感情,人也非常好,我们修理排的战士们都很喜欢他。战友们给我发的连首长穿军装的照片里,我还认出了雷修正指导员和李世荣指导员,我在汽车连时,他们都是副指导员。听说雷指导员在西安见过我父亲,这事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的。那时候,部队领导干部和战士们同甘共苦、身先士卒。在襄渝铁路建设期间,他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和他们相比,我们偶尔遇到的一点困难、受的一点委屈,根本不算什么。常言道“吉人天相”,我也相信好人、善良的人一定会有好报。

襄渝铁路建设时期,我在汽车连的三年里,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我记得有一次部队吃饺子,好像是春节的时候,大家都特别高兴。按照事先的安排,汽车连各班拿着打饭的盆,依次到炊事班领取面粉和饺子馅,随后全班一起和面、擀皮、包饺子,大家有说有笑,气氛十分热闹。我们包好的饺子放在铺着报纸的床板上,排列得整整齐齐。包饺子是我的强项,速度特别快。我们班的“大脑袋”——1968年入伍的江苏江都兵陈明山,主动要求去炊事班占灶台。等我们抬着包好的饺子去炊事班煮时,看到陈明山正躺在灶台上“占位置”,说我们班要先煮。不知是谁说了句“二锅饺子,头锅面”,他立马站起来说:“那你们谁先来,我们班煮二锅。”(其实正确的说法是“头锅饺子,二锅面”,看来他被大家忽悠了)我之所以对这位战友印象深刻,是因为他就是我们十五班的“大活宝”。我经常和他开玩笑,他也爱和徐积根抬杠。1973年3月,汽车连有一批老兵复员,陈明山也在其中。他站在大卡车上,刚摘掉领章帽徽,就高声喊着“向解放军学习”,把两边欢送的战友都逗笑了。陈明山战友离开部队时,穿走了我的一件线背心,就当是我送他的礼物。他送给我的一张照片,我至今还保存着。这是我在部队第二次吃饺子,第一次是在卫生队。
我在汽车连还有一位战友,叫欧阳衡平,湖南衡阳人,1972年初到汽车连修理排,和我们排的陈和平战友(已病故)是一个班的。(陈和平和我们班的电工张明川战友都是石家庄铁道兵学院的,陈和平口琴吹得特别好,不幸在青海牺牲,现安葬于青海刚察烈士陵园。)欧阳衡平的父亲是49团总工程师欧阳信,1949年入伍的湖南兵,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我在部队时见过欧总,他个子不高,但精神头很足。虽然我不如对包团长、刘副政委那么熟悉,但对欧总的印象也很深。后来听说,1972年夏天,欧总在襄渝线旬阳吕河车站工地被起吊的预制板砸伤,险些牺牲,之后就离休了。我记得欧阳衡平刚到汽车连时,说着一口湖南普通话,待人亲切,娃娃脸上总挂着笑,我对他印象很深,大家也都很喜欢他。1972年年底,他调到铁11师53团汽车连驾驶排当兵,退伍后回到湖南衡阳,曾任衡阳百货公司党委书记。2020年11月,包团长的儿子(曾在铁11师53团机械连当兵)做东,我们在西安长安大饭店重逢,这是我离开部队、离开汽车连后,第一次见到曾经在一个锅里吃饭的外地战友。

我在汽车连还经历过一件事,叫“点验”,就是对部队的战备和安全情况进行全面的清点检查。我不知道后来部队是否还开展过这项工作,当时要求所有人把箱子等个人物品全部打开接受检查。我记得当时战友们主动上交的子弹,就装了好几脸盆,其他班也有上交的。此外还有一些违禁品,但数量很少,具体是什么东西,我已经记不清了。1971年“9·13事件”后,部队要求将所有子弹上交。晚上站岗时有枪,但没有子弹。我在汽车连晚上站岗时,很喜欢背56式冲锋枪,一拉枪栓子弹上膛的动作十分顺手,可没有子弹后,再背冲锋枪就没什么优势了。战友们开玩笑说:“背冲锋枪还不如带根棍子,遇到情况还能抡两下。”于是,我晚上站岗就改用56式半自动步枪了。虽然半自动步枪也没有子弹,但起码有刺刀,关键时刻比冲锋枪管用。
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连队营区里有一只小黄狗,战友们说它是炊事班的。我有时会偷偷喂它,慢慢就和它熟悉了。每当我半夜起来站岗,它都会跑过来卧在我身边,一有动静就竖起耳朵,警惕性很高。晚上站岗带着它,我仿佛成了在边防线上巡逻的战士,心里还有点自豪感。后来战友们告诉我,这只狗可能是老百姓家的,跑到部队里来的。

我在汽车连时,检验站站长叫张福义,个子高高的,陕西长安人,也是一名军工,咱们《辉煌汽车连》一书中有关于他的记载。我们每次修完车,都要经过他的检验。我现在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他试车的样子。离开部队后,我们见过一次面,还在西安“白云章饺子馆”一起吃过饺子。张福义老战友回到西安后,被分配到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劳动局)开小车,如今已经退休多年,今年八十多岁了,身体依然很好。
2018年7月,我专程前往旬阳吕河寻找汽车连的旧址,见到了原汽车连修理排1966年入伍的安康恒口兵程开绪副排长。我在西安时听说他娶了吕河“一枝花”陈三妹,到了之后才知道是谣传。开绪战友告诉我,陈三妹已经过世了。想当年,号称吕河“一枝花”的陈三妹,可是我们汽车连小伙子们的“梦中情人”。我和程副排长聊天时,多次提到检验站的张福义站长,看来张站长在战友们心中也是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

49团汽车连,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在这里,我还想说说我们大修班(十五班)。大修班承担着全团汽车的大修任务,任务紧张时,基本上三天就要完成一台车的大修,工作极为繁重。汽车连大修班就是我在部队的家,战友们就像我的亲兄弟、家人一样。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工作、同娱乐,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大修班期间,大家对我都非常好,这份情谊我永远铭记在心,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些朝夕相处的战友。我们班是个大班,编制36人,如今分别五十多年了,我始终记得的战友有刘军驰、刘新国、程俊、甘秋来、李勇、安晓明、苏浓灿、徐积根、陈明山、屈晓松、李春伦、高贵林、孙志荣、曾道成、吴锡山、黄世忠、刘小康、蒋次忠,还有我敬重的老班长张学明,以及两名军工——天津的张师傅和南通的吴师傅。目前已知张明川、梁友贵等7名战友已经病故。还有几位战友的名字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即便记得名字的,也有很多失去了联系,比如刘军驰、刘新国、陈明山、李春伦等人,不知道他们近况如何。常言道“一日战友,一生兄弟”,何况我在这里待了三年,格外珍惜这份战友情。
这些战友,都是我在逆境中经受过考验的生死兄弟,我终身难忘。山东淄博的曹建国战友拉我进汽车连群,至今已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这段时间里,我感慨良多,得以重温军旅梦、再述战友情。在汽车连,还有许多战友让我今生永远无法忘怀,比如林达钦、曹建国、郭学珍、马德全、陈树建、高玉良、苏炳南、欧阳衡平、王西京、常正生、江保宏、白西民、申铁船、邓福民、吉苏烈、李忠良、张志雄、秦恒骢、李永成、王建初、龚登云、朱正才、周炳华等,还有我敬重的老首长杜玉良连长和雷修正指导员。

1973年5月,我离开汽车连,被分配回西安,进入陕西省交通厅下属的国有企业工作。一年后,汽车连转战青海刚察哈尔盖。有一次我去青海湖游玩,听说汽车连曾在刚察驻扎过,便专门开车在刚察县城转了一圈,追寻老部队的痕迹。
永远的铁道兵,不变的战友情。衷心祝福我的战友们晚年幸福快乐、健康长寿!我撰写的《战斗在襄渝线上的记忆》系列文章,今天就到此搁笔了。我先后写了5篇,回忆了自己参加襄渝铁路建设各个阶段的真实经历,这些文章在铁道兵网上发表后,阅读量已达四万多人次。这既是我对襄渝岁月的追忆,也是对历史的敬重。感谢曹建国战友(原铁道兵10师49团汽车连,现铁友全国文旅康养服务中心副秘书长)、袁武学战友(原铁道兵10师47团,火箭军西安工程大学教授,大校军衔)、付锁战友(原铁道兵10师48团,系列电视片《三线学兵连》拍摄者)对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编辑:向日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