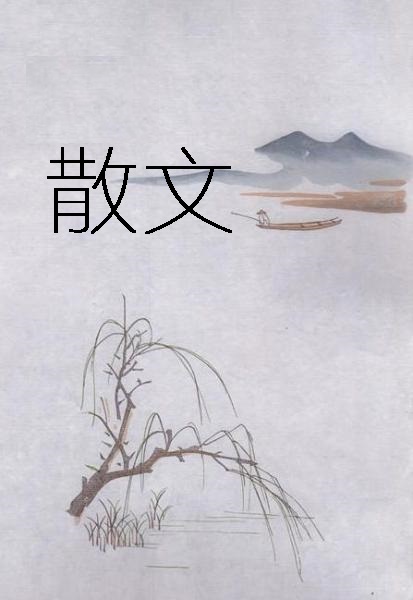铁道兵文苑
文汇报笔会集萃精选 《 哈尔滨看冰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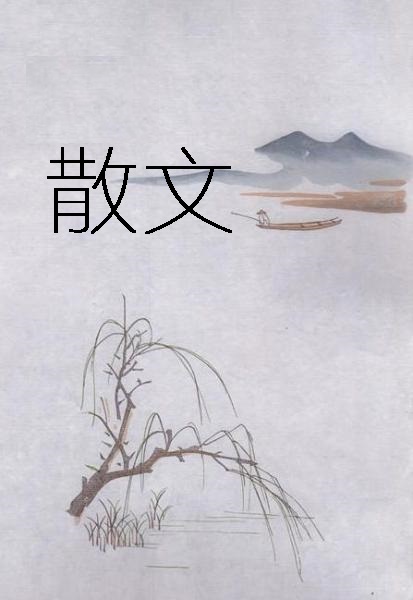
文汇报笔会集萃精选
哈尔滨看冰灯
施叔青 台湾当代女作家
上铺的墙板整夜叮当作响,再是用穿了好几层衣服、裹着厚被的身躯抵住车墙,响声依然,怀疑我们的卧铺是在火车的尽头,任由夜里更为凛冽的风雪拉扯,才会感到车厢随时要被拆散开来似的。
全副武装,连口罩也派上用场,下了火车,才走两步,拎行李的手,隔着衬毛的厚皮手套,冻得刺痛,指头发僵,失去知觉,人没出火车站,已经领受哈尔滨的威力。
蒙头裹脸冲入国际饭店的旧楼,旋转门内黑沉沉的,大堂挤促狭窄,完全没有大酒店的气派,后加的电梯,仅够两三个冬衣臃肿的乘客。
虽是火车上整夜没得好睡,却也难以忍受房间内的幽暗死沉,一把拉开热气管子上的窗帘,豁然一片白光,马路对面,一座顶部呈圆穹窿的俄罗斯建筑,暗红色的葱头尖顶,萧瑟地插入灰茫茫的寒天,行人们不疾不慢地在雪地上走着,隔着双层厚玻璃,听不到一声响,自觉像是被流放到异国边境的女囚,困在破败的旧楼里,窗外所见这一角是我所有的人间。
光是这样乱想,也使我从脚底冷了起来,急需有一杯热水来暖暖手。三脚桌几上的热水瓶是空的,走廊上不见服务生的踪影。隔壁会客室杳然无人,整整齐齐一排热水瓶,一副开会在即的架势。北方人喜喝淡茶,我把两杯的茶叶倒成一杯,"偷"了一杯热腾腾的茶,捧回房中,女儿担心隔壁少了茶叶、茶杯,人家会找上门来。
怠工的服务生连开水都懒得供应,主人的盛情却从早餐就显露无遗。雪白台布的餐桌上,发现烫平白餐巾,连中式早餐都讲究用布餐巾,不知是否沿袭白俄贵族的遗风?
准备一偿宿愿,在去兆麟公园看冰灯的途中,饱览哈尔滨街景,哪知车窗结了厚厚的白霜,完全把我们与外界隔绝了,女儿借来一把削水果的小刀,刮去玻璃上的白霜,象卖火柴的女孩,扒在窗口,从凌乱的线条空隙,窥伺外边一小片的屋角与枯枝。
我则垂头冥想萧红的一篇散文《他的上唇挂霜了》,描写两人借住萧军教武术的学生的家,也是"玻璃生满厚的和绒毛一般地霜雪。这就是'家',没有阳光,没有暖,没有声,没有色,寂寞的家,穷的家,不生毛草荒凉的广场。"
她站在小过道窗口等萧军,她肚子很饿。学生的二姐"蓝色的大耳环挥荡不能停止"。和萧红谈胡蝶的新电影,被盼回来的萧军"上唇挂霜了,他从口袋取出烧饼来给我吃,他又走了,说有一家招请电影广告员,他要去试试。"
这还不是最惨的。为了逃婚,萧红离开呼兰的家,被她中学老师始乱终弃,怀着孩子回到哈尔滨流浪。她"用夏季里穿的通孔的鞋子去接触着雪地",下雪夜,在街上找寻当晚投宿的所在,甚至羡慕老家的马房和狗窝:"挂在马房里,不也很安逸吗,狗睡觉的地方,一定有茅草,坐在茅草上可以使我的脚温暖。"
白俄开的"来顺旅馆",住着妓女、无赖,房主把大腹便便的萧红囚禁在内,留下来当人质,要她"赚钱"还她欠下的房饭钱,据说萧红那时还染上鸦片瘾。
"来顺旅馆"必然已成陈迹。萧红透过《国际协报》登出求救的诗,被萧军救出后的日子还是不好过,文人煮字不能疗饥。
车窗刀削的痕迹,又被冰霜封住了,最后一根火柴也熄灭了,蓦然回首,奇迹出现了,车后头的窗,像雪水刚淋过似的,清晰地映显倒退的街景。
"……哈尔滨最热闹的中央大街,俄国式的建筑,"显然不以开车为满足的司机,自动充当导游:"……挂红灯笼干什么?餐厅呀,挂一个表示只卖水饺、面条小吃,两个灯笼的里头有炒菜,再多挂一个就吃酒席了……"
萧红在商市街天天挨饿:"我拿什么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可以吃吗?","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
车子停在松花江畔,"天河"冰封了,白茫一片,我却想着萧红,总爱很女性地借用家禽来比喻自己落难的窘境:
"落下井的鸭子一般,寂寞而隔绝!","饿在笼中的鸡一般,只想合起眼睛来静着、默着,但又不是睡","看到列巴圈(面包)正象遇见了桑叶而抬头的蚕一样……"
从没见过如此苍白无力、影子似的太阳,才下午三点半钟,落日已像一圈薄薄的彩纸,毫无份量地浮在江上,灰茫茫的天被映得惨凄凄的。
松花江还没过完,落日已经完全失去威力,连影子也隐去了,仅剩一晕模糊的淡红。斯大林公园叠银砌玉,沿斜坡用冰块砌成的万里长城,一路蜿蜒下去 若非身上臃肿,女儿真想一路顺溜下去……
才一转眼,"战胜洪峰"的冰雕塔,里头连串的绿灯泡,亮了起来,刹时间,整个园子异彩纷呈,没点灯的飞禽走兽暗了下来,寂然地蹲在一旁,哈尔滨的夜,过早地撒下了。
东北的冰灯,原是穷家老百姓过年过节的装饰,利用取之不尽的冰雪,雕成玻璃一样的灯罩,点上烛火,挂在屋檐下,这种民间艺术的历史,可追溯至清朝。
一直到十多年前,哈尔滨市民巧妙地配合天然冰雪与灯光色彩,精雕出各式冰灯、冰花、冰盆景、建筑等造型,招徕了无数游客。
兆麟公园大门张灯结彩,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第二届的冰雪节,幸亏老天合作,元旦前后狠狠下了几场大雪,才使五日的点灯仪式如期举行,不必动用预备好的人造冰。
公园内,假山、凉亭、花坛埋于冰封之中,踏上结冰的小溪,如履平地,来不及想象春来时,园内另一番景致,立刻被冰砌的奇景吸引了过去,随着迎宾的冰花盆景,穿过姿态各异的动物长廊,看那跨河飞架的冰桥,尽头是玲珑的亭台楼阁,冰凿的飞檐斜翘,刺入雪封的夜空。
童话里的城堡,藏着鬼怪妖魔,本以为进了拱形城内,便可缘着绳梯攀爬上去,营救囚困塔顶的长发公主,才一晃身,人已出了城堡,望着层层上叠,像模像样的冰块,不免失笑出声。
随着红、绿异彩冰灯绕转,夜完全黑的尽了,国际冰雕比赛的作品,任由观众评头论足,加拿大队刻的一只四不像的怪物,和女儿指指点点,笑弯了腰,再抬起头,却为眼前的奇景所怔住了,惊喜地大叫:"快看,是树挂!
一大丛柳枝结上一簇簇、一串串的冰晶,缕缕白玉冰条,披挂开来,像进放的银色烟花,坠下前一刹那闪烁异常的光芒。
刚才松花江畔,冷得只顾缩头缩颈,没去注意十里长堤的玉树银枝,借此驱前细看,忘了脚下冰滑,人往前一仆,摔了一跤,连带女儿也跌了个四脚朝天,军大衣太厚,一点也不觉得疼痛,挣扎了半天,才由别人拖起。
一枝开花的桃花,斜插白苍苍的柳枝树挂,格外显眼,寒天地冻哪来花开?心中一狐疑,才察觉自己身处一片花树丛中,颤颤雪枝上红点斑斑,一定是纸扎的假花。距离"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是太早了些。
初见冰灯树挂的兴奋消退了下去,这才匀出眼睛来打量游园人,多半成双的年轻人,男的深色毛呢大衣,女的鸭绒服色彩鲜艳,除了我们,再也看不到草绿、土蓝的布料军大衣,当地人嫌土,穿在我身上,别是一番滋味。
女儿看他们个个行色从容,手上还拿着冰棍,她勇气来了,站在点着煤油灯的摊贩前,对红橙橙的冰糖葫芦不屑一顾,却买了一枝冰棍,我凑兴咬了一口,牙齿软了,冰棍完好无缺,女儿用舌头舔了半天,才说是黄豆做的。
(本版编辑: 老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