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友故事会~144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一群特殊兵,上了特殊的战场,表现的非常的特殊
——题记
特殊战场上的特殊兵
文/谢自强
(一) 不可闪失的文件包
我非常特殊,人高马大,身强力壮,一米八二,全连最高,战友们喊我“高个”,陈建中见我喜欢作曲唱歌,按“高个”谐音,给我起了一个雅号“高歌”。我是连队“特殊1号兵”。
我是1965年8月入伍的。我是独子,按当时的政策,独子可以免于服兵役的,我却坚决要当兵。可是父亲是“黑五类”之一的右派分子,政审差点没通过,因我在校品学兼优才招征了我,进入广州军区通信训练大队无线电报务班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军区通信团五连担任无线电台见习报务员。
1966年10月,我部调一批电台出国作战,我积极请战。那时文革风起云涌,查出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在右派分子的帽子上又加了1顶——解放前在国民党空军油库任职员。如此一来,我的政治面貌是“夜里进山洞——黑上加黑”。由于我请战态度非常坚决,加上我的无线电报务技术在同期人员中首屈一指,终于被批准成为誉称的“五个伟大”(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代表,奔赴援越抗美战场,我决心以我的荣誉来洗刷父亲身上的“黑色”!
这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一个特殊兵,上了特殊战场的事。
在整个越南战争中最为惨烈的1966年至1968年,在越南的土地上,我荣获嘉奖,还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但这仍然远远不够,我要热血洗门楣。
记得进入越南的第二年——1967年5月的一天,李冬球台长命令唐方敏和我,去大队司令部取无线电台联络文件,那可是机密中的绝密。那天,唐方敏斜背上手枪,我斜背着橙黄色的牛皮文件包,与唐方敏一起向远在三公里外的指挥部急行而去,在司令部保密室办完文件交接手续,当即返回。来时顺利回时遭,遇到了敌情,山野响起了警报声,美国轰炸机又来轰炸了。当时,我们刚行进在一块狭小盆地里,一片空旷,毫无可遮掩的隐蔽物,我与唐方敏急忙弓腰跑到斜坡上就地卧倒。在美机的呼啸声中,我和唐方敏意识到不能两人都牺牲了,立刻分散开来。美机轰炸了,敌机低空从头顶飞过,产生的负压让人无所适从,好像把人耳的耳蜗吸取来似的。
敌机的轰炸倒是无所谓了,司空见惯。只是我当时想法很多很复杂,我意识到我今天可能要光荣了,真的要“热血洗门楣了”?如果我光荣了,或我负伤不省人事了,来现场的不是我军人员或越南人民军人员,而是越奸或敌特,会拿走我的文件包,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我意识到这一点的严重性,将文件取了出来,藏在上衣口袋里,并将文件已经转移在我身上的情况,告诉了离我50米远的唐方敏,我就准备坦然的迎接敌机的下一轮轰炸了。这时,我又心生烦恼了,如果我负伤了,身上流血势必会渗透衣服,会不会污染了文件?文件搞得模模糊糊看不清楚,也更麻烦的,我赶紧将文件从衣服口袋取出,重新放回文件包,把文件包隐藏在一颗杜鹃树丛中,扯了几把草把它盖住,又告诉唐方敏:“文件包就藏在杜鹃树下”。
不一会儿我又“胡思乱想”了。
我刚满18岁,心智未完全成熟,所以七想八想:“我光荣了,唐方敏也光荣了,我的战友们来了,不知道文件包藏匿处,那可怎么办呢?”于是,我又将文件包取了出来,冲唐方敏喊:“唐方敏,我把文件包拿回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隐藏。”唐方敏比我大两岁,早我一年入伍。他很平静的喊我:“谢自强,不要慌,一般情况下,敌机轰炸完了就走了的。”他这一喊,我的心情稍微平静了许多,于是,我将文件包放在胸前,然后人趴在地上,把文件包压在身下。敌机几番俯冲轰炸,幸好炸弹没落在我们头上。直到警戒解除,我俩安然无恙,返回了驻地。
现在谈起这段往事,云淡风轻,笑我当年少年不成熟,真正的不成熟。但那些“错综复杂”的“胡思乱想”,却证明了我对责任的忠诚。也因此让身陷围城的父亲在政治上得到些许安慰。证明了特殊年代特殊兵,在特殊的战场上的特殊表现、用我的热血,洗刷我谢家门楣的表现。


谢自强与战友张毅(左)、李高(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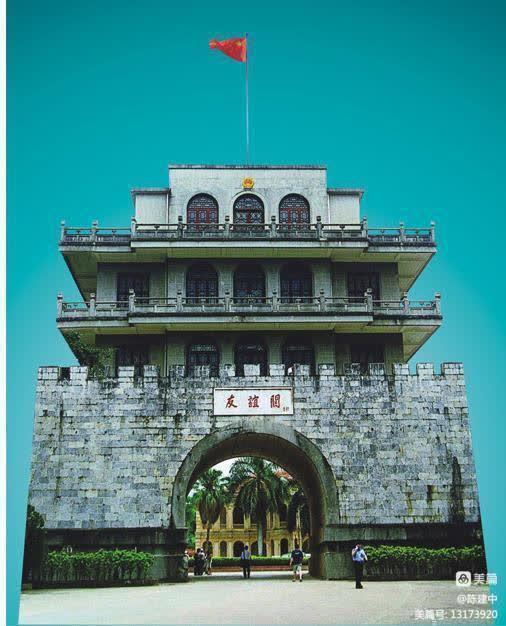
请看下期
《谢自强讲故事之2》

编辑:开门见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