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另一片天空
原创 |铁道兵张衍海
18
因为有这层关系,入伍后,我和雪儿开始通信。
通信不是很多,断断续续。有时候一两个月一封,有时候两三个月一封。
最长的一次,有半年多的时间没有接到雪儿的信。
一一那段日子,正是她父亲病重、病危、病逝的过程。我一点消息也没得到,雪儿没告诉我,在信上只字未提。不知是何原因……
我写给雪儿的信,有长有短,很想说说在部队里的事儿。但我们担负的战备铁路建设任务,具有对外保密的要求,所以,避而不谈。那谈什么?就谈谈大东北吧一一雪儿没来过,冬天的东北像一张大白纸,满纸都是她没见过的事物和情境;还有,我在这片雪野上的感受与回望一一
雪儿:
又是一年飞雪时,一张白色的大纸,铺天盖地,邀我书写封存已久的回忆,记下留待今后偶尔的阅读一一
幼时在东北,游玩在桦树林中,踏雪在银装大地,溜冰在三九湖面,行走在脚下响着咯吱咯吱的踩雪声的马路上,我分明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纯粹的东北人。虽然周围有许多人都是山东老乡,他们都坚称自己是山东人,但前辈人闯关东的故事仿佛发生在前个世纪。那份萦绕在父辈心头的游子对故乡的牵念,早己在东北的朔风呼啸里离我远去,在关外的飞雪飘扬中与我作别。于是,我融入了东北,融入了这块不是我的故乡我却把它认作故乡的地方……
后来,由于家世的原因和境遇的变故,我才不得不离开东北。关里的家乡、前辈的故土,像一个强大的磁场,把我们全家吸了去。
那一年,我十二岁。
当我跟着父母、牵着弟弟们的手,一步三回头离别东北时,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还能回来……我知道,这样的怀念将会伴我一生。一次又一次冬去春来,当柔和的暖风拂绿关里的柳梢,那一年又一年窖藏心底的怀念也已酵成了一缸醇酒,醉了我,也醉了梦里的春色。老家的青山秀水在我朦胧的眼里叠印着长白山的白雪、兴安岭的松涛、松花江的飞鹤,映现着黑土地翻滚的泥浪、雪原上飞驰的爬犁、桦树林喧闹的鸟鸣……
或许是由于父母的这个抉择在具体操作上存在疏漏,或许是因为他们当时压根儿就没去想此举会带来什么后果。草草率率千里迢迢地举家迁回山东,城市户口没能落上,好歹算是“天无绝人之路”一一农村老家的生产队并不拒绝我们,我们具有了和祖上一样的身份一一地地道道的农民。
少年的记忆里,关里似乎比关外还要寒冷(在老辈人的意识里,关里关外以山海关为界)。冬天,坐在摆着十几张破桌子烂板凳而且四面透风的教室里,脚上起了冻疮,手背裂出了血口子。我白天到一所破庙改建的小学去读书,晚上替刚娶了媳妇的一个青壮劳力给生产队打更,图的是能在不花钱的油灯下看书。所幸这样的日子没有白熬一一转过年去的夏天,我成为那所农村小学当年毕业班里唯一考入县一中的学生……
上中学的日子,肚子最难受。天天吃饭的时侯,就啃发了霉的窝窝头或煎饼,都是用地瓜面做的,颜色发黑,口感极差。我家离一中有六里多路,当时没有自行车,更没有公交车,只能住校,每个周末回家拿一次干粮。有一次从家里返校的时候,遇到了暴风雪。有不少学生因为天气不好而未能及时返校。我是回校学生中的一个。我们的行动感动了校长,他特意安排大伙房烧了两大锅姜汤,里面还有面疙瘩,辣椒面也撒进去不少。我们不嫌辣,觉得那是这辈子喝的最好喝的姜汤,这也是少年时代我最感到幸福的一天……
几年后,上天没忘了眷顾我,东北也在适时召唤我。在我不再是一个懵懂少年的时候,朝思暮想的大东北一一我回来了!

在穿上军装的岁月里,我喝过三岔河、六股河、老哈河的水,翻越过辽南、辽西、辽北的山。前面的路还很遥远一一远方还有昭乌达、哲里木,科尔沁大草原;无边无际的草浪和沙海,飘若白云的羊群,内蒙古汉子放声高歌的长调和弹奏拉响的马头琴声;从草原大漠北部边缘再往北望,是连绵起伏的兴安岭,是奔流不息的松花江,还有无边无际的大森林……
在大河上架桥,我仿佛觉得桥梁就像我的胳膊,欲把这块辽阔的土地拥抱;在群山里铺路,我仿佛觉得钢轨就是我的旅痕,欲将生命中所有的精彩追寻……
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于生我养我的大东北,我离而复归,欲舍不能。虽然身为筑路人,漂泊一生,四海为家,用脚步丈量过的地方将会越来越多,唯独对于大东北,自有一种别样的情愫。这里有永久不泯的影像,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这里有穿透山河的呼唤,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弦和耳畔;这里又如破土而生的种子,早已在我的生命中扎根发芽了一一岁月愈长久,便愈加枝繁叶茂。
……
路远
某年某月某日
有些话,写在纸面上,也是多余的。有些话不用说,不用写,用心去感知,永远忘不了。关于我,我不想多说什么一一我的生命和生活,就是自己给自己的注解。从小到老,一个生命的过程,一种生活的轨迹。
我曾是一粒极小的种子,被埋在漆黑的山地里,陪伴我的只有冷寂。
我不甘冷寂。于是,我破土而出。
我焦渴地仰望蓝天,蓝天若无其事,毫无表情;我期盼着阵阵长风,长风拂袖而去,对我不睬……
我明白了:要想生存,只有靠自己!
我用顽强的根,紧紧抓住脚下的岩缝;我用笔直的躯干,扬起生命的绿色之旗。
因为我生在谷底,峰顶的小草才耻笑我一一长得真矮;叽叽喳喳的麻雀也喜欢踩在我的肩上,对我评头品足……
我面对无聊的饶舌,忍受着内心的委屈,沉默着。
终于有一天,暴风雨来了!
我张开双臂,接受暴风雨的洗礼。
小草被山洪卷走,麻雀们也不见了踪影。
我留下来,还要生存下去。裸露的根,是我裸露的情愫;满身的水珠儿,不再是酸楚的泪滴……
我不再怕什么了。
朔风送来新一年的请柬。大片大片的雪花,在我周围旋转。我虽然不太喜欢单一的颜色,但是除了雪白。
因为:白,它从不对其它颜色造成干扰。在一张白纸上,你尽可以随心去描画,尽情去涂抹……
就因为这样,我接受了那份请柬一一
亊先声明:在银色世界中,不改我一身青翠。
我的生命是从脚下的山地起源的,尽管它贪瘠,我也不离;我倔强的禀性是跟峭岩学来的,虽然常遭冷落,我也不弃。
我仍在成长,我渴望长成大树……
和喜欢“炫富”的那类人不同,我不怕露穷。把自己家境穷困潦倒的一面,把许多的不如意、不时尚、不乐观的层面,不去刻意地隐瞒和遮盖。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穷则思变,有什么不好?
栽在花盆里的盆景,煞是好看,成不了材。
实在地说,我是一个“挺不靠谱”的人。你无法拿一个通常的标准去衡量我。曾经,我帮连里一名半拉文盲战士写过情书,是寄给他家乡一位姑娘的。
有一天,他来找我,此时已经把一只脚踩进失恋的泥坑里了。
“文教,你得帮帮我!”他沮丧地说,满脸都是万恶的旧社会。
我问:“咋回事?”
他说:“未婚妻,不干了……”
“要散伙?”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忙,还非帮不可。

他把底儿全兜给了我,还有那女青年的来信和照片一一原来,女方嫌他文化低,没情趣,所以……
我问:“她是什么文化?”
他说:“和我一样,小学三年……”
我一听,有门儿!
心里有底了,就劝他:“男子汉大豆腐,何患无妻!”
接下来,我帮他分析了形势,估计目前还不存在情敌。即使有,也争取把人夺回来,甭管是人质也好俘虏也罢,只要不是叛徒。下一步怎么办?采取攻心战术,循序渐进,以守为攻,是为上策。也可以围而不打,先晾晾她。照常写信,她一封你一封,不卑不亢,不温不火,也尽量不提感情的事儿,就当那封绝交信你没收到(我估计火力侦察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不予理睬)。这边,加紧学文化,从练字写短文开始,尽快消灭错别字。与此同时,报请钟副指导员同意,我把他列为连队文化夜校重点学员,制订计划,定向帮扶……这等于战前训练,临阵磨枪(我告诉他,不是咱现在用的枪,这枪不能磨;磨的那是冷兵器时代的枪),不快也光。快则三个月,慢则半年一一训练完毕就展开进攻。到那时要集中火力,把你的优势充分展现出来,我给你提供炮弹!
一一所谓“炮弹”,就是我把情书底稿给他拟好,他抄一遍,推入炮膛,直接发射就行了……
“要是夺不回来呢?”
“废话!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多的是……”
“那行,试试!”听口气,他的战斗意志上来了。
这小子也争气,不到半年,立了个“三等功”。喜报寄回家,情书也跟上了,那女青年审时度势,山门大开,二人重归于好。
那名战士脸上已是云开雾散,变成解放区的天。
再见了面,我就开始“使坏”一一
有事没事就逗逗他,反正,他的秘密都在我手里攥着,他受制于人。
那伙计无奈,半喜半忧地求着我说:
“文教,咱不带这样儿的一一捉鬼是你,放鬼也是你!”
知晓内情(包括略知一二)的人,都哈哈一笑。
我心里挺滋润,这家伙都用上词儿了,还挺恰当一一有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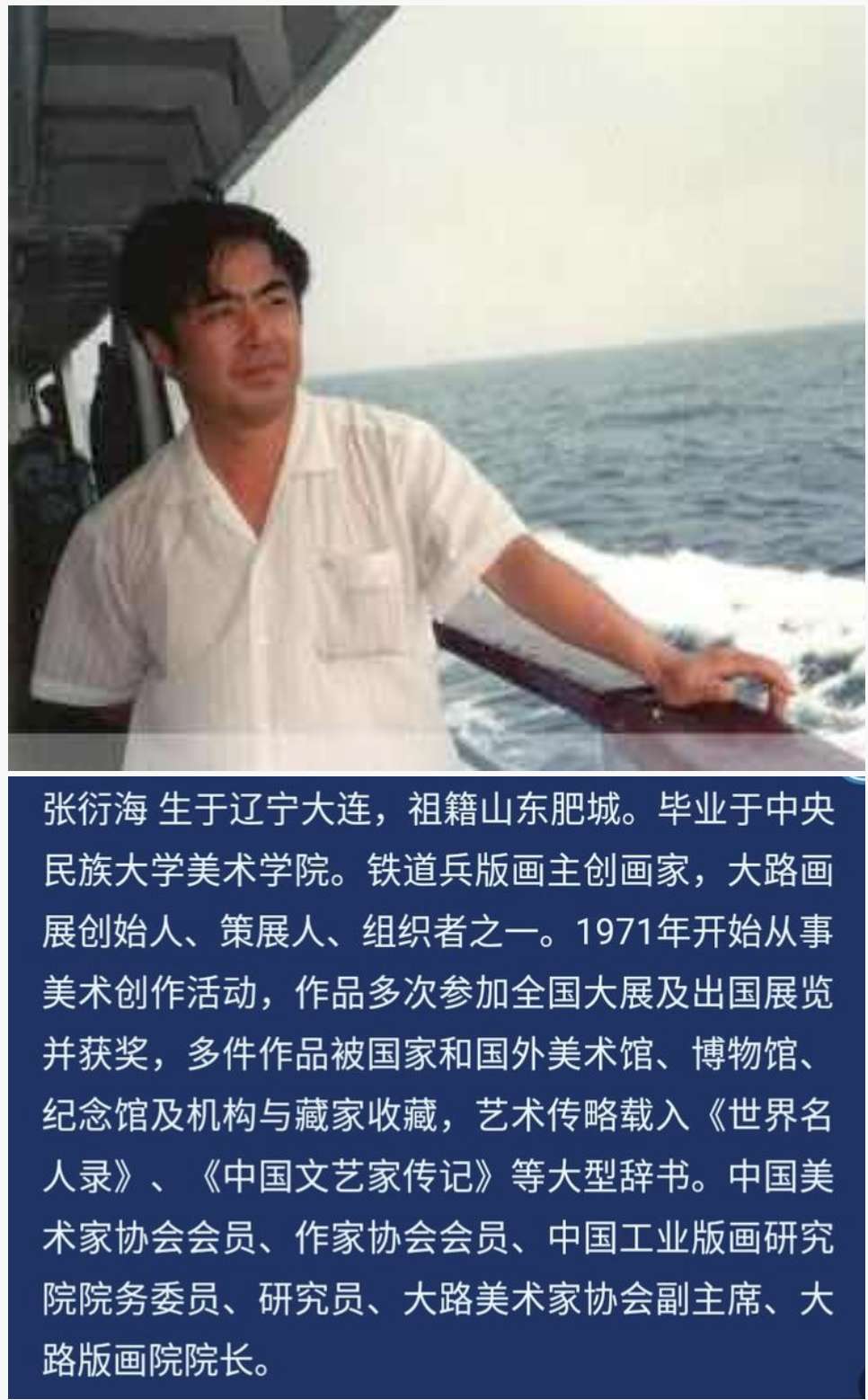
未 完 待 续
编辑:向日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