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架子队里的农民——工?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许多新名词,“农民工”就是其中一个,而且还是中国特有的。农民和工人本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农民就是务农人,工人就是做工人。当农民和工人合二为一之后,你就弄不清他倒底是农民,还是工人?
吴佩印就是这样的一个农民工。他的确切身份是中国铁建第十八局集团公司拉林铁路工程指挥部第二项目分部安全总监,即使他已经被公司正式聘用为合同工,他已经进入到第二项目分部领导班子成员之列,但是他说,他觉得他的骨子里仍然还是一个农民工。
下面,我不得不用大段的非文学语言来叙述一下吴佩印这样体制外的农民工进入体制内的背景。
中国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铁路建设突飞猛进,尤其是遍布全国四纵四横的高速铁路网络快速建设,铁路建设的投资连年大幅增长。资料表明,“十五”期间,国家铁路基本建设投资2700亿元,平均每年500亿元左右。到了“十一五”期间,铁路建设跨跃式发展,规划投资2.95万亿,实际投入4.2万亿,其中基建投资超额比例接近90%,年均投资超过“十五”期间10倍多。“十二五”期间,铁路建设与投资经历了大起大落的V型反转走势。至“十二五”末期,铁路建设投资再回历史高点,连年投资规模达到8000亿元,年均通车里程达到8000多公里。
新建铁路项目井喷式地快速上马,一时间令工程施工单位应接不暇,一个铁路工程局此前每年平均承包铁路工程量只有区区数亿元,一下子迅速猛增到每年承包数十亿、数百亿元的铁路工程。大量的铁路建设工程承揽下来,自己的施工力量却又一时跟不上,于是,一个叫做“架子队”现象的产物在铁路工程及至整个建筑行业出现了。
说到架子队现象,还得先说说它的前身。
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大批富余的农村劳动力都以青壮年农民为主,纷纷离开农村走进城镇,参加城市建设。而城市处处都是大工地,急需大量的劳动力。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叫做“包工头”的新 “职业”应运而生。包工头并没有工程投标的资质,却能从工程单位那里分包到一些工程。包工头也没有公司单位,却能将进城来正着急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召集到他的旗下,将自己分包到的工程活儿派给他们干。包工头就这样恰到好处地在劳动力供需双方之间起到了重要的关联作用。
但是,工程转包、分包的弊病接着就显现出来了,一些素质不高、不懂技术的包工头偷工减料、违规操作、事故迭出,豆腐渣工程频繁曝光,还有包工头克扣农民工的问题也屡屡发生。2005年,国家建设部下发《建设部关于建立和完善劳务分包制度发展建筑劳务企业的意见》,对施工企业劳动用工制度进行转型改革,规定工程总承包企业不得将工程违反规定发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包工头”个人。《建筑法》更是明确规定,违法转包、分包工程的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
在施工企业用工制度改革的新形势下,当时的国家铁道部创新了架子队这个铁路建设市场劳务用工模式的改革新尝试,专门出台了文件,积极倡导架子队的管理模式。所谓架子队,就是工程作业队的基本框架是管理监控层加上作业层的组成模式,也就是说,工程作业队由施工企业搭建一个负责施工管理的管理层“架子”,劳务企业提供负责施工作业的劳务人员,其中大部分都是与劳务企业签订有劳动合同的农民工。这样就从法律形式上把包工头彻底排除在了现场作业序列之外。
于是,世纪之初,在中国铁路工程建筑领域出现了一个独有的“一队两制”的“架子队”现象:在同一个施工作业队,发挥施工管理作用的“骨架”是工程承包企业的人,实际发力现场作业的“肌肉”是劳务企业的的;“骨架”人员都是体制内员工,包括队长、工程师、技术员、安全员、质检员、实验员、材料员、领工员、工班长等,而“肌肉”力量都是都体制外的农民工,包括开挖工、爆破工、钢筋工、混凝土工、电焊工、架子工、模板工、起重工、普通工、安装工、钳工、电工等。体制内员工和体制外劳务工最大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工资收入、福利待遇上的不同,最根本的还是身份上的不同,前者是工人,后者是农民—工。
吴佩印这个农民工就是这样进入到中铁十八局隧道公司施工作业架子队的,参加过多个铁路、公路建设项目,一开始从架子队的开挖工、架子工、混凝土工、钢筋工等工种干起,从架子队的“肌肉”一步步干到架子队的“骨架”,当过架子队管理层的工班长、领工员、质检员、安全员等,直到被公司正式聘为合同工,成为体制内员工,已经担任中铁十八局拉林铁路工程指挥部第二项目分部的安全总监。但是,吴佩印还是忘不了他当农民工的这段珍贵的人生经历,忘不了还是农民工的这些工友。他常说:“是农民工的这段经历锻炼了我,是中铁十八局对农民工的重视培养了我。我是从农民工里成长起来的,因此,我为农民工骄傲,为农民工自豪。什么时候我都忘不了——我是农民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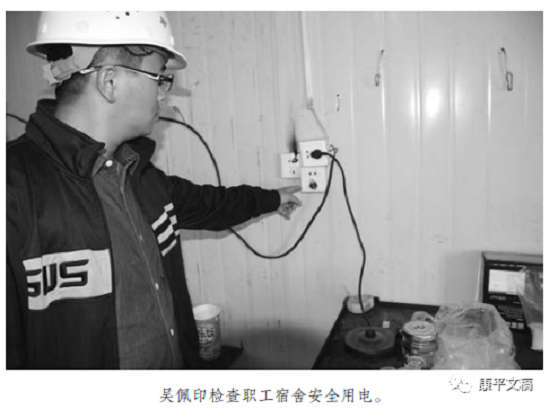
原文链接:点击查看
编辑:兵心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