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的还是襄渝铁路建设那个年代的事。
记得进入隧道施工那阵子,是三班四运转,也就是说,每天施工出峒到下一个接班,换休的间隔时间仅仅十二个小时,除去来回路上和吃饭时间,最多也就是十个小时。到了冬季,连队热水供应不及,大家基本上很少洗澡,为了方便起见,一身棉袄下面就是一件单背心和一条内裤,从掌子面下来,个个都像是掏炭的,穿着被汗水浸湿的黑黢黢棉袄,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抓紧扒拉两口饭,汉江边上擦把脸就钻进了被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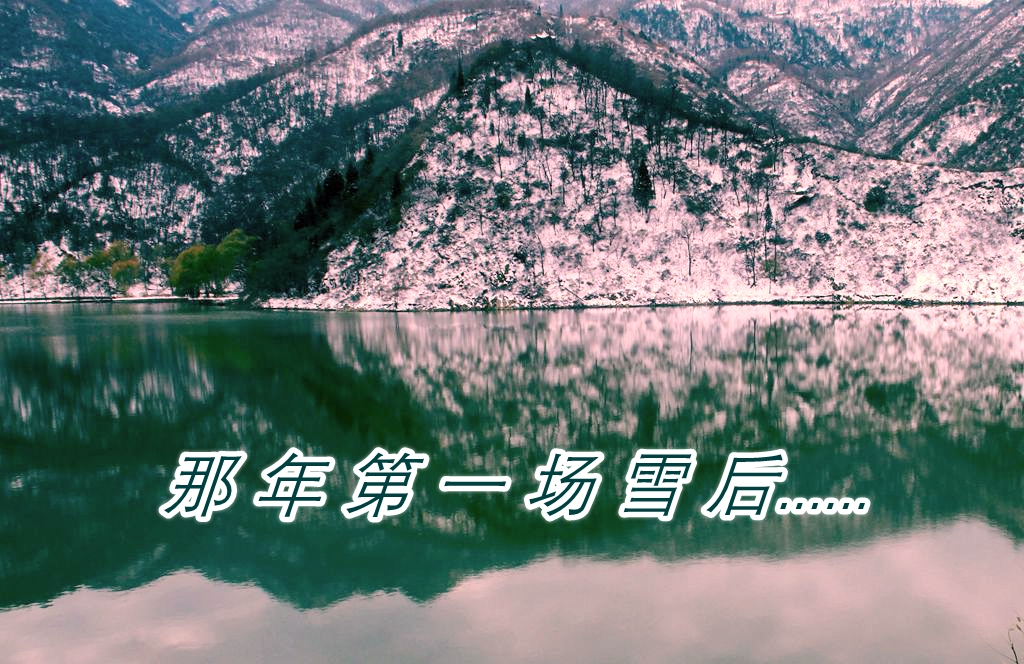
不用说,被褥被单成什么颜色都能够想象出来。
那年第一场雪后,紧接着就要到春节了,我和副班长姚存兴商量了一下,并在班务会上告诉大家,找一个晴好的天气,把我们班的苏书关留下来,为全班同学拆洗被单,咱也好干干净净过新年。起初都很赞成,可到了实施的那一天全体反对,这个反对意见,我和班副都很理解,大家太累了,深夜零点下班,睡觉已经是凌晨了,现在天还没有亮,又把一个个拉起来拆被褥,谁能没有怨言,有个人就直接顶起来了:“班长,你懂不懂,腊汁肉夹馍黎明的觉,这是最香的时候,你把……”其他人就把被子裹在身上围坐在那里,就是不挪窝,表示抗议。班副急了:“反了,反了,你们真是披着被子上天,张狂地没领咧!”我又接着给大家说:“咱闲话少说,都配合一下,赶紧把自己的被褥拆了,把被单交给书关,裹着棉花套子继续睡。”
就这样,我和班副姚存兴帮着苏书关,把拆下的被单装进每个人的脸盆,送到汉江边,又赶忙从炊事班要来一盆热水把洗衣粉化开,分到每一个脸盆里。三九天的汉江岸边结着一层薄冰,河道上寒风凛冽,吹在湿淋淋的手上像刀割一样疼,只见苏书关挽起袖子,穿着胶靴嘎扎嘎扎踏过冰层,站在离岸大约三米的水中,把我俩洗好的被单放在水里搓净,然后用石头压上让水流漂洗,我再看他,整条胳膊都冻的红肿。
苏书关回过头看看我俩,笑着说:“班长,你和班副回营房吧,再过一会,你们又该接班了,抓紧时间还能再眯瞪一会,今天有你俩帮忙,我肯定能完成任务!

(自右至左,前排苏书关、张建西,后排王勚斌、吉农)
我回到营房的时候,太阳已经老高了,站在门口望去,阳光下汉江波光粼粼,河滩上晾晒的几床花花绿绿的被单被石头压着,四角在寒风里扑扑抖动。
我感觉还刚刚睡下,通信员的起床哨就响了,接着排长走进来,看到我们都是裹着棉花套子,打趣道:“今天怎么啦,白花花一片,都成杨子荣进到林海雪原啦!”
开饭时,班副把饭菜送到苏书关跟前,让他休息一会再干。在集合去工地前,全班同学挥舞着手中的工具,朝着汉江异口同声地大喊:“书关,辛苦了!”此情此景,叫我的心里哪能不酸呢。
我们下班回来,苏书关已经把被单全部收回,跪在床上正给大家缝被褥,我发现他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流淌,捉针的手呈紫色,并不停发抖,我用手一摸,他从头到背全是虚汗,苏书关在汉江边的寒风中耗了一天,他病倒了。
同学们急忙从苏书关手中夺下针线要自己缝,可是这些小伙子哪里干得了针线活,王勚斌对着微弱的灯光,连针都纫不上,急的团团转,自言自语地说:“要是我妈在跟前就好了,也不用咱吃这苦,受这难。”就这轻轻地一句话,让大家都静默了,有几个同学的眼睛里闪着泪花。说真的,我当时也想哭出来。突然,朱家驹忽闪着眼睛说,我有个缝被褥的好办法,说着起身到连部,借来订书机,把剩下的几床被褥“钉”完了。
第二天,苏书关烧的厉害,大家七手八脚把他硬是拽到连队医务室,班副姚存兴按着他的肩膀说:“你今天不要去工地了,好好休息,你的活儿我们大家都替你干了,不要让大伙儿为你着急。”
苏书关稍微退烧了一点,他又回到营房,待大家去工地的当儿,他硬撑着爬起来,把昨天“钉”好的被褥摊开,用牙拔掉每一个订书针,针线重新走了一遍,坚持完成了全部拆洗被单的任务。
在参加襄渝铁路建设的两年零八个月的艰苦岁月里,这件事情可能早已被我们忘却,可是那种团结互爱,坚韧不拔的精神,却牢牢地铭刻在每个战友的心上,当我们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心里总是暖暖的。
2023年1月5日
编辑:岁月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