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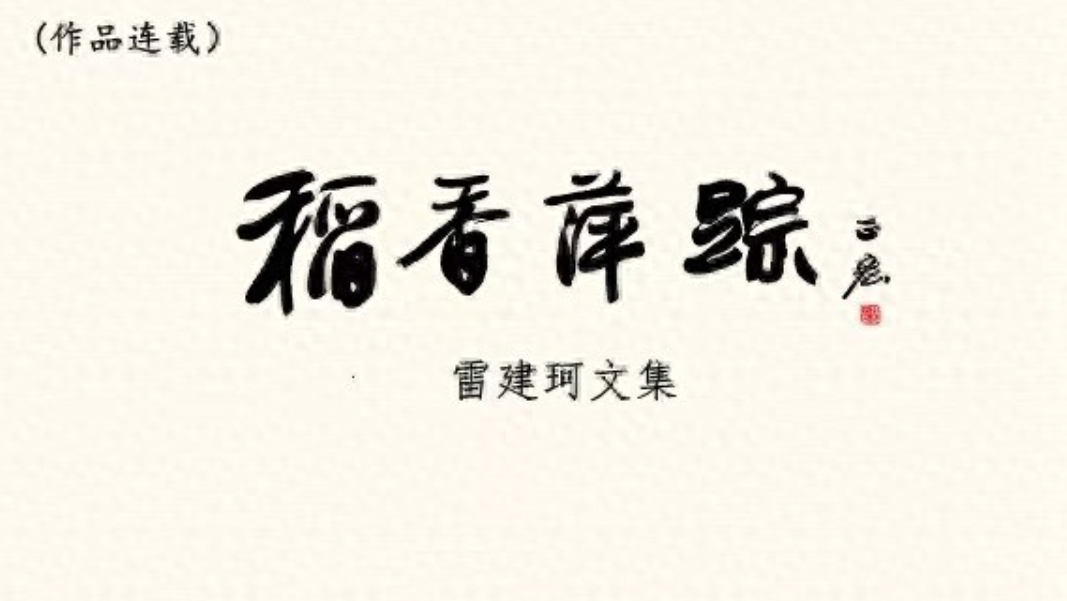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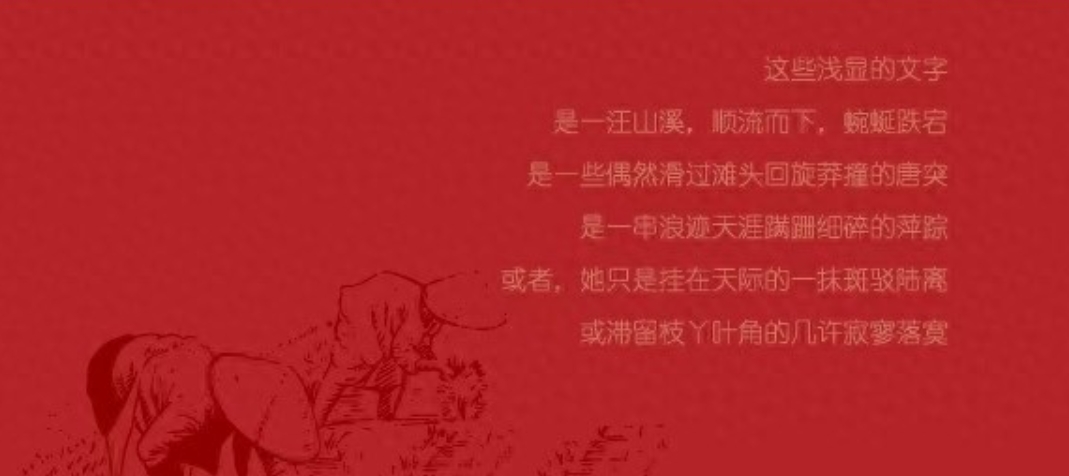
《稻香萍踪》雷建珂文集之十四(一份久远的回味、那些行将消逝的记忆)
一份久远的回味
借金洲抵京返回途中的龙城停留之际,和双平一起结伴游览了五台圣境。金洲和我是发小,长大一些一个班上中学,后来一起入伍到了同一个部队服役,转业后在一个单位,可谓一生不离不弃的哥们。
金洲和我并不在一个村,他家是和我八里开外南寨的舅爷做邻居的。我从小喜欢舅爷,喜欢跟了奶奶去舅爷家。舅爷善良勤劳,自小老实木讷,耳朵又背,舅爷是奶奶三姊妹中的唯一的弟弟。舅爷双亲早逝,家境贫困,为人老实厚道,一生没有娶妻成家。舅爷也很喜欢我,舅爷家住的是窑洞, 我每次跟了奶奶去舅爷家,舅爷都很开心,不是带我去半山坡的地里摘苹果,就是在沟边窑畔打枣子给我吃。我很爱吃舅爷亲手做的蒜水扯面,至今还能记起三十多年前舅爷做的蒜水扯面的悠长美味。舅爷年届中年的时候,抱养了姨婆的小儿子(我叫作福学叔的)外甥为子,以便老有所依。福学叔 很聪明,成年后一直在村里当干部,成家后小两口孝敬老人,日子过得颇有起色。记得我九十年代初结婚那天,已经八十多岁的舅爷,蜷着像只虾一样弯曲的腰身,拄着拐杖颤颤巍巍挪了八里远的路程,来参加我的婚礼。老远看从见远处艰难而来的舅爷,我不禁泪眼婆娑,赶紧飞跑到远处的路边,搀扶了老人一路到家,将要耗尽体力的舅爷安顿到奶奶炕上歇息。

舅爷常年一人生活,里里外外全要自己打理,舅爷特别讲究,还记得舅爷的窑院内外总是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从塬下车路往南就是南寨梁,其属于秦岭山麓的余脉地段,沿着掩映在果园深处的一道漫上坡的小车路,不几步就是村口,进入村口再上一段坡路,再沿河沟边下去,是一溜坐西向东三四户人家,西面都是窑洞,家家院子面对着河沟。下到坡底尽头就是舅爷的院子。院子内坐西面东并排凿了一大一小两孔窑洞,前面是一个南北顺沟狭长的小院子,院子面东是一条常年流水的深河沟,时常听得见哗哗作响的流水声,舅爷在河沟边缘窑洞对面的位置修了两间又低又矮的厦子房,窑院位于河西岸上,窑院前后树木参天,郁郁葱葱,很有情趣。后来因窑背崖上雨水渗漏,窑洞后半部垮塌, 不能再住人了,舅爷和福学叔就住到了原来做厨房的厦子房内,而尚未垮掉的窑洞前半部分则用来做堆放粮食和杂物的储藏间了。
福学叔唱过戏,先是在村剧团作司琴,弹的是一架很气派的洋琴,唱的戏全是当时的样板戏。再后来福学叔就在村里作支书,几任村班子齐心协力在全村发展林果业,在井索沟里栽种梨树,在南寨梁和平川种植优质苹果,生产队里和社员先后都富裕起来了,舅爷家便和邻居们先后都在坡下临近公路的村街修起了楼房。社员们走上致富路,过上了好日子。舅爷九十年代中期去世,我没有能够回去给老人送行,是后来才听家里说起,一份愧疚便被深深刻在了心间。
南寨谢家是大户,奶奶在族内人缘极佳。奶奶每次回娘家总会在大大小小的各叔伯家走走,看望老人,叙谈家常。那些我称其为舅爷的奶奶的平辈们,以及我称其为叔叔的奶奶的侄辈们更是对奶奶爱戴有加。四时八节的总会提了用大口袋装得鼓鼓囊囊的梨子或是苹果来家里看望奶奶。当时我们兄弟年岁尚小,家里有这些好吃的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不亚于过节,客人还没走碍于情面不可轻举妄动,但孩子个个心里早已对那些好吃的虎视眈眈,垂涎欲滴了。那时候的水果真是原生态的,一些苹果梨子放在屋里,连院子里也能感受得到扑鼻的香味。还记得小时候经常一起玩耍过的伙伴,除了金洲,还有秦州、安科等等,当时都是几岁最多十岁左右的伙伴,而今几十年过去大家都已是年过半百,大都儿孙满堂了。

岁月如水,人生苦短。在这利益金钱至上的年代,回味那些珍贵甜蜜 温暖的往昔,总有一些情谊值得咀嚼和沉淀。我们不应淡忘那些过往的温 馨,看重亲情、珍惜亲情,让我们并不富余的人生岁月更加多彩而充实。
2016年秋郝家坡
那些行将消逝的记忆
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我在老家西河滩的一所由古庙改建的七年制学校度过了懵懂的童年时光。四十多年的流光飞逝,沉淀了太多曾经的过往,也消磨了太多不知愁苦的困顿,唯有一些为数不多的碎片不时在脑际划过。

这是一隅曾经辉煌,让诸多军阀官商趋之若鹜的知名村落 ;这是一方依山傍河,风景如画的鱼米之乡 ;这是一片有过无数历史名人曾经涉足的风水宝地。学校就坐落在与岐山安乐相交的界渠东边,界渠以西为岐山所辖,界渠东边就是眉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学校属于公共资源,学生可以跨界就近选择学校入学,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合适的学校。这样,我们这所中等规模的学校里就有了界渠两边分属岐山、眉坞两个县区的学生。最热闹的时候除了就近的界渠西边岐山的一部分学生外,附近村落的贾家寨、积谷寺、石龙庙和斜峪关五个村的中学生也划归于此就读。而各村均设有小学,自然无需舍近求远了。小学各班级里的学生除了一些岐山籍和个别外村籍的以外,绝大多数为本村的学生。
学校是解放初期由政府出资,在原来一座古庙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最初的村公所也在此办公,整个学校占地二十亩,坐北面南。北半边为古庙宇原来的建筑,靠北院墙正中的是原来古庙的大殿,加上西北角新修的三间小房子一并作为学校的灶房,正殿西侧靠南坐西向东的是一座新盖的三 间的教室,我的小学二年级就曾在这间教室度过。正殿前,座东朝西的是一座连体的十多间的古庙里的老房子,当时这些房子屋檐处的卯榫结构的挑檐及屋角随处可见一些五光十色雕梁画栋的古迹,这些房子作为老师们的办公室和宿舍。上面这些建筑以正殿为中心自然形成一个不算大的小院落。 小院落南侧和正殿遥遥相对的便是学校的露天大舞台了,舞台坐北向南, 前面就是占整个学校一多半规模的大操场。偌大的操场上,靠西围墙边的一溜有几株合抱粗的合欢树,而东边则是一溜碗口粗细枝叶繁茂的枫树。每逢秋季到来,整个操场笼罩在一片火红与碧绿的海洋中,美不胜收。那一片渐次由绿变红、在秋风中频频招手的枫叶,和对面一树树绿叶映衬下团团火红的合欢花,成了那些岁月里最美好最鲜艳的定格。舞台西边和舞台并排的是一栋老房子,这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教室。沿着舞台和操场东侧的所有区域是在古庙宇基础上新扩大的范围,靠南与操场以渠和中心路为界,分别修建有东西走向的一片排列整齐的四栋八个教室,北侧是一片小杨树林, 最北边的老房子和东院墙之间是一片菜地。菜地里有一株两人合抱粗的又高又大的冬青树,一年四季郁郁葱葱,冬青树旁边的老房子是井房,水井和井房是古庙里原来就有的老设施。淘气的同学会三两个伙伴一起,偷偷折了冬青树的枝叶,突然混在柴火中塞进灶房里的灶膛内,听一阵噼啪作响,挨一顿灶师傅的责骂,然后便是心里乐着悄没声息地四散而逃。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校生活非常热闹。舞台上不时在演出一些由身着绿军装的红卫兵、红小兵们手捧语录本、挥舞红绸带边唱边舞的舞蹈和一些样板戏之类的节目。有一出当时十分流行的《大红枣儿甜又香》的歌舞节目,内容是歌颂共产党的,还记得歌词大意为:
“大红枣儿甜又香,送给咱亲人尝一尝。一颗枣儿一颗心,哎嗨哎嗨心心向着共产党……”。舞蹈由十几个高年级的女同学表演,记得还有和 我一个生产队的巧玲姐。那些女同学个个身穿色彩鲜艳的水色衣裤,大辫子上扎着红绸花,画着眉腮,十分俊俏。每人手捧一个装满红枣的竹篮子在舞台上整齐地边舞边唱,个个婀娜多姿,热情洋溢,那场面很是热闹感人,至今记忆犹新。
学校最破最老的建筑就是舞台和操场西北角的一年级教室了。小时候 我不是个灵光的孩子,就在这间当时只有黄泥墩架上木板搭成的简易课桌的破烂而简陋的教室里,我竟然糊里糊涂坐了两年。班主任是刚当上民办的黄海绪老师,黄老师通过努力先后完成了省教育学院本科和研究生学习,又被选入一所省重点担任把关数学老师。当时的情形已全然没有印象,后来三四年级的时候黄老师还给我带过语文。也就是这个时期发生的一件小事至今记忆犹新。四年级的时候,班里流行一种画画的风气,就是把小人书里的人物临摹在十六开的纸上,然后用蜡笔或水彩着色,画好后贴在家里墙上来欣赏。起因是一个叫做虎成的同学,(我曾专门写 过一篇关于他的文字《虎成》)家境非常贫困,父母亲有病,哥哥残疾,需要经常耽误上课时间去帮妈妈干活。他年岁于我略大,个子也高,身材很威猛,看似愚笨,其实非常聪明。我们一节课没拉过的,作业也会时常出差错,而虎成就是几天没来上课,作业也完成得非常好,这令当时的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我要说的是,虎成还是画画的好手。小人书上的画面不论多么复杂,只要看一眼他都能够一丝不差地临摹出来。记得虎成当时画过一幅小人书上很复杂的绘有古代建筑物的画面,全是用线条表现的,竟和小人书上的一模一样。而我则对一本《三国演义》的小人书尤其痴迷, 还有另一本《西游记》,这些在当时均属违禁之列。后来就陆陆续续临摹了一些这两本小人书上的关羽和猪八戒等等内容的水彩画,但总觉得画得不尽人意,要比虎成的差得很远。一次我刚画好一幅画,还没来得及收起来,内容是关羽身穿盔甲,挥舞大刀的英武形象。不成想竟被突然进来上课的黄老师逮了个正着,捅了大娄子。当即被黄老师点名站起来,狠狠地批了一通 :“你一个平时表现还算不错的学生,不好好学习,竟一天到晚画这些帝王将相、封资修的东西,纯属不务正业”云云。这是由一年级班主任黄老师而联想到四年级时的一段经历,而消磨了我两年漫长时光的一年级竟毫无印记了,足见当时的我的确愚钝。

到了二年级就有一些美好的记忆了,记得这是第一次享受有了课桌板凳的学校生活,桌凳都是一些低矮规格的, 比起一年级的黄泥敦来已是十分的优越了。同班印象深刻的诸如当过班长、嫁给后来当了老师的李小林的刘月仙,还有个头高挑、学习出色、后来嫁给中学老师的月琴、还有腼腆内向的老师的女儿水婷,还有一队的黄海棠、八队的唐淑艳、七队的张乖秀等等。月琴因为和老师常有互动多有联系,老师从政,月琴开了一家颇有名的广告公司,事业甚是红火。黄海棠、唐淑彦鲜有了解,据闻她们都事业有成。张乖秀学业有成。不过多年后,竟有消息说乖秀得病殁了,真是难以置信。我二年级的班主任是老家南寨万户、嫁给本村四队刘家的黄全会,一位善良的女老师。黄老师从二年级一直带我到了四年级,应该是我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一位老师。我这 点还算扎实的拼音基础全得益于黄老师的悉心教授,以至于受益至今。当时的黄老师年轻而富有朝气,齐耳短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时常在棉衣外 罩一件淡蓝色与浅色相间的对襟夹袄,显得干净利落、泼辣干练。黄老师一双灵动的眸子透着对学生的慈爱,她对犯错误和调皮捣蛋的学生又格外 严厉。那时正值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说是人民公社化大家心情舒畅,但生产力低下,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尤其是我们乡下的孩子,家长们都在忙于劳动生产孩子又多,根本无暇顾及孩子的个人卫生,男孩子更其如此。学校教育是要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除了检查学生作业和劳动技能外,对低 年级学生也会偶尔检查一下个人卫生。记得一个冬天的早操后,所有班级的学生都进教室早读了,而黄老师偏偏留下我们班里的全部男生,在操场上靠近舞台的空旷地带,让我们十几个男生一字儿排开,要求大家一一脱了鞋子检查大家的双脚卫生情况。难堪尴尬的时刻来到了,我和另外两名同学“有幸”被选为最不讲卫生的典型。当时已经八岁的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恨不得钻入地下。结果尽管难堪,处罚却是温暖的 :去老师的房间把脚洗干净。现在的黄老师早已退休,我回去探亲偶尔也会见到,几十年过去,从老师身上依然可以感受到曾经的恬静干练和慈祥温暖。

三年级的时候班里来了几位界渠西边老庄的新同学,有见得最多的男生刘得堂、李福全和后来很少见到的女生邵彩凤、李青彦、杨腊香等等。其中李青彦一直和我上到四年级才转回本域。还记得当时个头很高、块头很大的李青彦一直很关照我。她和我同桌一年以上,我的座位多在里面靠墙,她则在靠过道一侧。我每次出进她总会像一个大姐姐那样不厌其烦地照顾我。彩凤因和本人妻家有些缘故,偶尔能够听到一些风闻,据说她婚姻多有坎坷,两年前去参加和她同村的我的外甥女的婚宴时,没想到竟在酒席上见了一面,看似情形尚可。
在小学还算腼腆的我,还是干过些不太体面的勾当。其中有两件事情让我至今无法释怀,愧疚难当。
水清是老师的孩子,自小家境优越,冰雪聪颖。隐约记得是在四年级前后的一天,好像是个春天,一直印象不错的女生水清不知因何让我非常生气,具体原因和细节已经无从记起。以至于我在放学后提前赶回离两家都很近的一处岔路附近,站在路中间等着随后放学回来的水清,以便伺机实施报复。不一会儿水清果然出现了,又正好独自一人。面对一个弱小的邻家女子,当时的我居然毫无怜惜之心,余怒之下,竟真老老实实给了毫无防备的水清一个耳光。当时的水清在突然被袭、疼痛难当的情况下,并没有选择质问和还击,而是双手捂着脸嘤嘤作哭状。她自然没有理会我,而是冷静快速地离开,然后径自回家。回家后的水婷也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家长,我的家长此后并未一如我所担心地责罚过我便是佐证。正因如此,才叫我愈加惶恐不安,直至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一次,是三年级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是一个严冬时节,学校放学,正对着校门往南是一片棉花地,棉花地中间有一条田间小路,沿着这条捷径可以很快回家。大家依次列队前行,我前面走的是一队的李喜雀,后面是一大群男生。 不一会大家便离开了老师的视线,随之,有几个调皮的同学开始乘机打闹。推搡是最常见的游戏方式,而在密集的队伍中,作为八、九岁的孩子们,这些行为具有很强的蝴蝶效应。当时的我,显然大受感染,随之进入亢奋活跃状态。前面就是李喜雀,她小心翼翼的行走姿势,让我觉得十分可笑。这无形中加剧了我的冲动感,随即迅速推了喜鹊一把,意外瞬间发生。颠颠跛跛的喜鹊,随即失去平衡,重重地翻滚入高坎之下的棉花地里,大家随即一哄而散。喜鹊生性最是腼腆木讷、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但学习踏实。结果是还没等我到家,一顿严厉的惩罚已经在等着我了。

水婷和喜鹊住在一起,都离我家很近。毕业后我外出闯荡,没有再见过喜鹊 ;水婷倒是偶尔遇见过一次,呈憔悴之状,远不似以往。也知道水婷是嫁给了我另一个要好的同学科科的。科科曾在县里的水泥厂干得有声有色。最近一个偶然机会有了一次和水婷的电话联系,不想竟然碰巧她正 在和拉虎、藕莲、雅芳、虎生、林科、岁劳一干同学在一所乡间酒店里小聚。得此机会乘机和每人都说了几句,很是温暖。期间也旁敲侧击略微对四十多年前的愧疚有所提及,水婷也表示早就淡忘了,随之一笑而过。
2015 年 2 月 郝家坡


编辑:向日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