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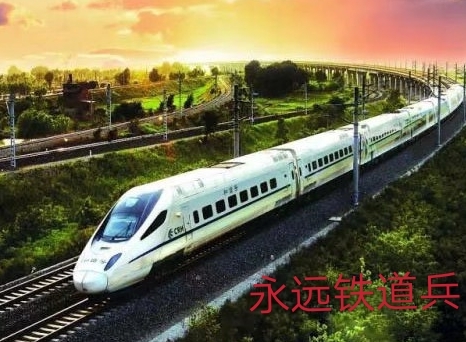
朱海燕 || 那江,那桥,那路……
作者 朱海燕
那江,那桥,那路……
铁道兵战友,被一个道路的“道”,拢在一起,心聚在一起,胜过血缘亲情,年年必有聚会。凑在一起时,激情的火焰便燃烧起来,必言那条江,必讲那座桥,必说由那座桥登岸,而延长的那条无尽的路,那是一条脚步走不完的路,是一条时间走不完的路,更是语言无法说尽的路……
那江叫松花江,是一条滔滔不尽的万古江河,孕育了一方万古搁浅的黑土地。

百年铁桥——陶赖昭松花江大桥断桥遗址
那桥叫松花江陶赖昭大桥,座落在中东铁路上。从这座桥开始,一支队伍的火红青春便扎根在祖国的大地上。
这座桥叫陶赖昭松花江大桥。1901年4月22日开工,1902年3月28日建成,中日战争又被炸毁。1940年日本接收中东铁路,重新建起一座下承式钢桁架桥,桥长987米,横跨松花江江面近500米。
战争中的毁灭与重生,写成它的命。
所有劫难都躲不掉因果的循环。谁也没有想到,这条江,这座桥,与一支修路队伍的命运紧紧相连。
这不是故事的新编,而是一桩历史造化的典范。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我12万大军挺进东北,以得东北而图天下。此刻国民党军没有闲着,1946年5月,以24.6万兵力进军东北,企图以内战的枪炮,守护垂死的江山。
他们向我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占领四平后,沿铁路北犯。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东北民主联军变阵地战为运动战,主动放弃长春、吉林等大城市,撤至松花江以北。

开国少将 苏进将军
1946年5月25日下午5点,东北民主联军最后一趟车列过江之后,掩护撤退的苏进将军下令炸断松花江大桥,迟滞了敌军进犯的脚步。
但未来的音符醒着。战士们用红漆在桥头岗楼上写下一行醒目的标语:“为了胜利,别看我们今日炸,还是我们明日修!”
也许,毁坏与建设从来就蕴含着一种哲学事件,山穷水尽处有一万种嘹亮,举着希望。炸桥时,苏进还是作战部队的将军,3个小时后,他走完142.2公里的路程,赶回哈尔滨时,他在车站候车室张贴的布告里看到,他被任命为护路军司令员。
所有的行为,无数的异常,叠加成后来的历史。炸桥,为了撤退;修桥,为了反攻。1948年7月5日,护路军扩编为铁道纵队,人民的解放事业像一轮太阳正在引体向上。为了配合大军反攻,成立25天的铁道纵队,将抢修陶赖昭松花江大桥的任务交给了3支队。那时,炸桥的苏进将军仍然是这支队伍的副司令员。
3支队队长彭敏说:“当初破坏得越严重,修起来越困难。”
他回忆,部队新兵多,懂技术的人,为了充实技术力量,从铁路调来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战争中的抢修对他们还是非常生疏的事。
1948年8月1日抢修工程开工。苏联专家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来到大桥工地,亲自指导抢修。1938年他毕业于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在卫国战争抢修与建设中,第聂伯河、伏尔加河、刻赤海湾之畔都留下他的身影。彭敏回忆:组织这个复杂庞大的工程,需要精湛的技术,周到精密的计划,需要人人知道自己的责任,需要坚强的劳动纪律……西林以他出色的才能,丰富的经验,耐心而严格地帮助我们逐渐熟悉掌握这一切,指导我们灵活地驾驶起庞大的工程机器。
潜水最艰难,但难不住修桥的人。一批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过去有的是养路工,有的是乡村的农民,他们在松花江的激流里训练。10米、20米,1米接1米的深潜里,录制着水下的苍茫。遇水架桥的壮志,满满住进他们的年轮。
王喜财的大儿子刚刚出生,媳妇不让他离家。他对媳妇说,我不能当“孬种”,一定要站在修桥第一线!他负责在桥梁上铺设线路。为躲避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施工常在夜里进行。一天夜里铺轨,天下着下雨,地面甚滑,他肩扛枕木一路小跑,扛了趟又一趟,不甚跌倒,枕木砸在腿上,小腿骨被砸断。
彭敏回忆:在学习掌握机械上,张景文分队为部队树起一面旗帖。过去,打桩普遍采用穿心锤,几十个人拉一根绳子,喊一句口号打一下,半天打不下一根。之后,经过研究、讨论、学习,摸透了机器的脾气,很快提高了劳动效率。
工地没有架桥机,东北铁路总局局长吕正操指示哈尔滨三十六棚铁路车辆工厂不惜一切代价,紧急制造一台80吨的架桥机,支援大桥抢修。
请记住,这是“铁道兵”的第一台架桥机,它以春天的速度,追逐奔腾的江河。

在苏联专家和铁路职工帮助下,1948年10月23日架通了陶赖昭松花江大桥,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
1948年10月23日松花江桥胜利竣工,24日举行了通车典礼。在通车典礼大会上,陈云赞誉这支修桥的部队说:“你们为东北人民修通了一条胜利之路!”
这支部队跨过了松花江,走过了陶赖昭大桥,站在了胜利的彼岸。但只是第一个“旗开得胜”!这只是第一个“马到成功”!这只是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的万里征途上盖下的第一个戳记!这支部队,随着长驱直下的野战大军,乘胜前进,入关南下。他们战斗在淮河上,修复了淮河大桥,而后修复了一座又一座大桥。这位修桥将军彭敏,后来离开了“铁道兵”,主政铁道部大桥局,修通了武汉长江大桥与南京长江大桥。

而这支部队,从渡过松花江那一刻起,它前方的道路就写满了漫长与艰辛,连成一片群山的苍翠与大漠的苍茫。这支修路的人,用生命与汗水,写满了一页又一页历史,写长了一里又一里道路。一次次青春被清空,他们把壮年与老人又握成了一个青春!一次次家庭被清空,在天涯、在海角,又安下一个家庭。
创业,是他们的金黄的驻足。
四海,是他们的新的家庭。
前方,是他们抵达的目标。
开路,是他们血淋淋汗淋淋的命名。

作者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开门见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