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咽喉的忧患》诞生的前前后后
作者 朱海燕
1988年,堪称是中国铁路的灾难年,重大事故频发不断,除了责任欠缺以外,我想把笔伸入到看不见的深处,进行一番反思性地剖析与解读。
那时,中国10亿人口,而铁路仅个月5万公里,至1990底,才达到53186公里,人均铁路长达5厘米,一根火柴棒的长度,这就是无情的现实。
人均5厘米的铁路,能担起沉重的国民经济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吗?
我想写一篇具有忧患意识的长文,定题为《五厘米的思考》。
准备动笔时,春节到了,我要赶回苏州与家人团聚。其间,还必须完成一部由我执笔的河北省副省长韩启民的回记录《年轻的时候》。
韩启民这个名字,读者可能不晓,说起她的丈夫,大家都会知道,那就是回民支队的政治委员郭六顺,司令员是马本斋。韩启民与郭六顺结婚3天,郭就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
韩启民解放初期做过石家庄地委书记,后任河北省副省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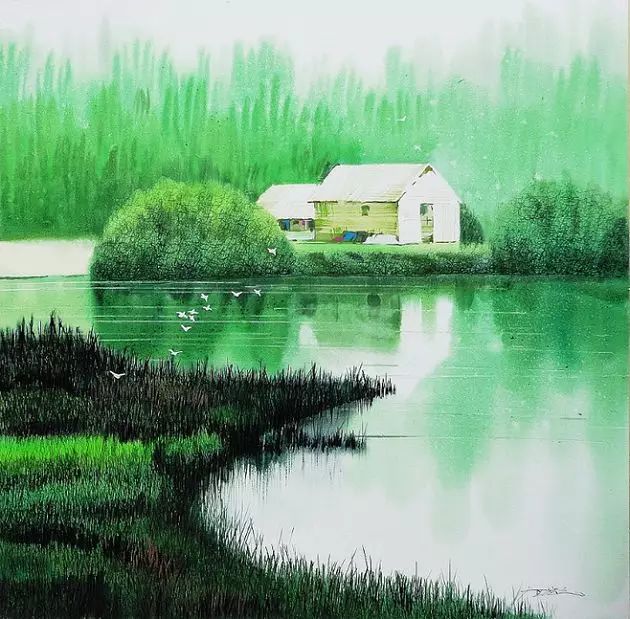
在苏州,年初一开始起笔,一直写到正月十二,17万字终于完稿。由于写稿的兴奋,后来的五天五夜几乎没合眼,怎么强迫自己睡一会都睡不着。
为了补充《五厘米的思考》的细节,书稿完成后,我又去了杭州。那时杭州正是甲肝大流行的时候。在此采访两天,乘120次列车返京。
当时北京对杭州、上海入京人员有强制性规定,必须进医院检查。我刚到京,就被医生逮个正着。一检查,转氨酶高达465,不容分说,把我送进了302医院。
既来之,则安之。心静下来了,脑子也不再想《五厘米的思考》了。几碗中药汤下肚,又睡了一个安稳觉,第二天再测转氨酶,又落到了正常的指标上。可是进来容易,出去不容易,是不是甲肝,都要住三个星期。
那时,我一人在京,妻子在苏州,单位是《人民铁道》报社,而我又住在中国铁建大院里。报社知道我已回京,但是到处找我又找不到,经过多方打听,方才知道,我被捉到302医院去了。待李丹副总编前往医院看我,已是我入院的第十天了。
我住院期间,《中国青年报》记者孙亚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他具有轰动性的长篇通讯《中国铁路悲歌》,文中所使用的数据,也都是我已掌握,并准备写进《五厘米的思考》文中的东西。孙文的发表,无疑我的熟烂于胸的《思考》全部泡汤。
在写这篇短文的前十天,我与亚明兄在南礼士路一家饭馆小聚,还谈及此事。我说,你《悲歌》的发表,让我的《思考》流产了。
孙亚明说,同样,如果你的《思考》先发表,我的《悲歌》也会死于胎中。
出院不久,严介生副总编派我去大同分局采访,他说,解剖了大同、沙城、丰台这条运煤专线,就等于解剖了困境中的中国铁路。
这同样是一篇极其重要的带有宏观色彩的长篇通讯。带着強烈的责任与使命,我走向大同。
大同分局长常国治说,我太忙了,没时间陪你啊。

我说,我不要你陪,但是你要同意让我去陪你。你去哪里,我跟到哪里,把我看成你身边的工作人员就行了。这样,他开会,我听着;他下基层,我跟着。只要他上班,我都在他的身旁。这样,我跟他整整半个月的时间,知道了他的甜酸苦辣,也摸清摸透大同分局和丰沙大全线的艰难困境。
真的不容易啊,一条几百公里的线路,承担了全国火力发电厂百分之五十的煤炭运输。就是说,如果丰沙大线路瘫痪了,全国有一半火力发电厂都要瘫痪。它承担着何等艰巨的运输任务啊。运输最紧张时,平均4分钟,要通过一趟运煤的列车。一个月,钢轨要磨损10毫米。每月都要不停地换轨。换轨还不能停止运输。如此紧张的运输,怎么保证它的安全?
大同分局在走钢丝!
丰沙大铁路再走钢丝!
采访结束后,标志着生活的积累,事实的积累已经完成。但是,这还不是动笔的时候,尚需文化与思想的积累,那段时间,我翻阅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马克思的《资本论》,我要从先贤哲人的著作中,找出支撑文本的理论灵魂。
孕育是漫长的。我终于在1989年的4月完成了这篇万字长文。
交稿后,我回安徽,又转道苏州办理爱人与孩子进京事宜。一天我从蚌埠火车站登上列车时,见几位铁路职工手里拿着4月30日的《人民铁道》报,不停地说:多年没见过这么好的深度报道了,向这个时代倒出了中国铁路的一肚子苦水。
我细看,一版头条上那篇长文,就是出自我笔下的《咽喉的忧患》。
文章见报后,大同分局党政工团致信人民铁道报社表示感谢。大同分局为这篇文章专门编印了单行本,发到班组。
大同分局局长常国治说,如果上级单位来大同分局调研,我什么都不说了,我给他们的就是这篇文章。
此文获1989年铁路新闻一等奖。
编辑:向日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