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梓祥:人老爱怀旧,现在铁道兵都老了,所以重访旧日军营与铁路工地的越来越多,但大都是团队行动。
车云华独自去襄渝铁路一次,“想了很久很久”。大段的抒情容易流于无病呻吟,但字字句句出自肺俯,因为那月河有酷暑、严寒中的鏖战,有担架军被下牺牲的战友……这都是青春的记忆。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这是徐志摩《再别康桥》中的诗句。车云华由重庆来,到襄樊去?或许更远处,也不可知。但时间成本、旅费成本……就为了看看月河的流水与月光,听听夜晚月河的风。不要以为铁道兵是五大三粗的莽汉,他们的劳动是诗,也有诗人的心!
月河一游,此生方得安稳,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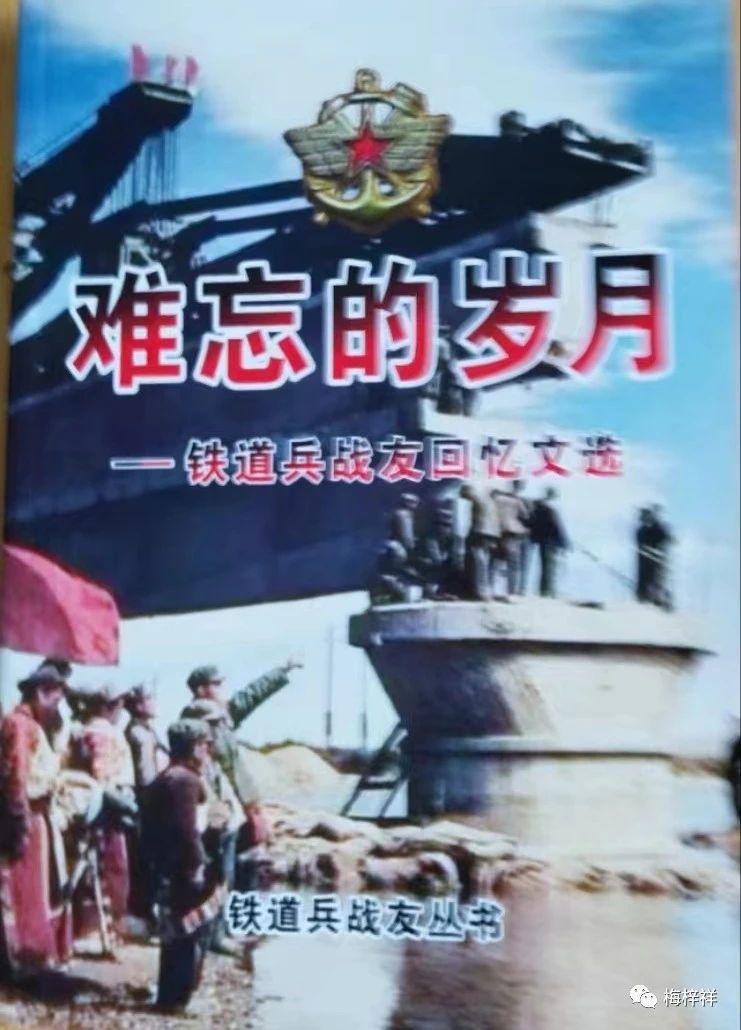
重返月河忆当年
车云华
时令已经是1997年的盛夏季节。清晨,绿皮列车从重庆出发后正向着终点站湖北省的襄樊疾驰着。这趟旧地重游的旅行,已经在心里想了很久很久。本想约上几位战友同行,但那时大家都在忙于生计,甚少联系,所以就只能独自上路了。
滚滚红尘,漫漫人生路,工农兵学商皆已经历,人生五味也已尝遍,一路 走来,当兵的岁月总是令人怀念!
月河,我梦中的月河啊,承载着我太多的青春记忆,天地之大美,唯有你能长留我心。你是如此的温柔,既便是洪水来临 也波澜不惊。你那弯曲的河湾,犹如少女曼妙的曲线;你那清澈的流水,好似姑娘明亮的眼睛。你总是那么平静地流着,流着,带着哀怨,带着忧伤。我知道,你是在为生活在两岸的人们的贫困而忧伤,你是在为孩子们消瘦的脸上写满饥饿而忧伤。多少次,战友们坐在你的身边谈心;多少次,我们坐在你的身旁为了分别而感伤……谢谢你,陪伴我度过了那段艰苦的青春岁月。
忘不了,那军民奋战的红五月,惊天动地的开山炮声仍在耳边隆隆回响;忘不了,月河两岸那整齐的营房;军人,民兵,学兵那青春洋溢的歌声总是令我魂牵梦绕!忘不了,酷暑笼罩着的陕南大地,骄阳下,我们在挥汗如雨地奋战;忘不了,深山峡谷中刺骨的寒风,漫天风雪中,我们在紧张 地训练,忙碌的施工……酷暑严寒何所惧,流血流汗为人民!当铁道线上的第一声汽笛响起的时候,我们又背上行装,扛起枪,奔赴新的战场。
一声汽笛的长鸣,列车已驶入了大巴山的腹地。放眼望去,绿色的河水依 山而流,但见峡谷、峻岭中皆是桥隧相连,看不见一块平地。我想,这里就是开国将领们在回忆录中称之为国民党统治最薄弱的地方之一了。当年,红四方面军就是在这块贫瘠的地区休养生息,在战斗中发展起来的。正是生活在这些穷乡僻壤上的劳苦大众,是他们养育、壮大了红军,养育了中国革命!我又在想,老一辈打下了江山,而我们铁道兵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铁路建设,不正是他们曾经为之奋斗过的事业的延续么。
列车在隆隆地行驶着,出了一个隧道口。啊,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在那连绵起伏的群山脚下的座座墓碑,那是我年轻的战友,还有那些投身于艰巨的铁道建设的人们,他们永远长眠在了我们战斗过的地方!
列车员告诉我,月河隧道快到了,月河车站是小站,快车不停。我的心情很是激动,月河,我梦中的月河啊,我终于要见到你了!屈指算来,襄渝线通车已二十四年了,我想月河两岸一定是楼房林立,工厂众多,一片繁荣景象吧。突然间,列车驶入了一条长长的隧道,没有灯光,只有从通气口漏进的一柱柱亮光。感觉是过了很长时间,列车终于冲出了隧道,紧接着就是一座很高的大桥,桥下的河水在平静地流着,两岸尽皆绿色,没有公路,更没有车辆和行人。过了大桥,月河车站四个大字一晃而过,站台上只有一位铁路职工手拿小旗在笔挺地站着,此外再未见一个人影,留给人一种凄清的感觉。
当天晚上, 住宿在安康火车站的旅馆里,心里总是觉得若有所失。第二天,一早就坐上了安康至伍里的班车,直奔月河。还记得紧挨着我们20连营房的是一座钢梁结构的公路大桥。这座曾经是车水人流的大桥啊,每天西安的女学兵、部队、民兵,他们在口令声中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嘹亮的歌声,在这座桥上走过,走向月河隧道工地。夏天的傍晚,人们在这座桥上散步,纳凉,谈心……阵阵河风吹来,令人倍感凉爽。如今,这座桥没了,只剩下河水中几个残破的桥墩!我站在河边,四周万籁俱寂,唯有东去的流水碰撞在桥墩上发出的些许微响。我的眼晴湿润了,我似乎听到了桥墩在叹息,它象一位久经风霜的老人,在叹息声中向我诉说着它往昔的辉煌。由于水太深,我又折回到了月河车站。不远处的铁道边上,站着十来位中年男女,过去一打听,才知道是1970年初中毕业后就从西安来月河参加三线建设的学兵。他们的眼圈红红的,好象刚哭过。他们这是旧地重游,是来月河纪念那段艰苦而又难忘的青春岁月的。我感觉在他们脸上还显现出一种自豪感,因为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有了一处值得回忆的地方。艰难的岁月总是能把人与人的心彼此紧紧联在一起,从此凝聚成一段终生的友谊!
走在月河大桥上,感觉头有点晕。向下看去,宽阔的月河瞬间变窄了许多,河水在两岸绿色的青纱中逶迤穿过,像一幅绝美的风景画。过了大桥,在月河隧道口旁找了个地方休息了一会儿,山风阵阵袭来, 令人心旷神怡。四周静悄悄的,昔日火热的施工场面尤如电影一幕幕地在脑海 中显现。
走在二十多年前的那条盘山公路上,感觉路面变窄了,路上有许多从 山坡上滚下的乱石,铁路通车后,看来这条路已基本废弃了。下山后,我终于 来到了我们20连过去的营房驻地。啊,这就是我记忆中的营房吗?!没有了, 全没有了!放眼眺望,紧挨着20连的18连、19连,学生连,民兵连,河对岸的女学生连,17连,营部,16连,团修理连……全是一片片的苞谷林,郁郁葱葱,长得甚是茂盛。正是玉米挂穗的季节,阵阵热风袭来,林中不时传来沙沙的声音, 仿佛是有人在向我诉说着什么。站在连队炊事班的旧址上,我向下注视着已是一片苞谷林的操场,一幕难忘的场景又浮现于脑海。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1972年深秋的一个阴暗的下午,厚重的乌云笼罩着月河两岸。操场上停放了许多担架,担架上的伤员,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有的用手支撑半躺着,还有两副担架上的人直挺地躺着、从头到脚覆盖了绿色的军被,我明白他俩已停止了 呼吸。活着的人在痛苦地呻吟着,他们黝黑的脸上满是死里逃生后的惊恐,这是从月河隧道的一次大塌方中抢救出来的战友们。月河水就在他们的近处静静地流着,月河在哭泣,它在为这些不幸的人们而伤心、哭泣。当救护车呼嘯而来又疾驶而去的时候,我颤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默默地祈祷着,我祈祷受伤的兄弟姐妹们能早日平安康复,我祈祷牺牲的同志一路走好,走上幸福的天堂。带着感伤的心情,我从苞谷林中慢慢穿过, 来到连部下方一块平坦的苞谷地,这里曾经是我们每天蹲在地上吃饭的露天饭堂。此时此地,触景生情,二十多年前的那段艰苦的铁道兵生活又湧上心头…… 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怕牺牲、无私奉献、不畏艰险、勇往直前,是铁道兵这支部队永远的军魂!当中央慰问团那高亢的歌声在月河两岸响起的时候,我们黝黑消瘦的脸上热泪盈眶,因为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了啊,共和国没有忘记我们!
绚丽的晚霞已布满天空,夕阳映照下的月河幻变成了一条金色的光带。河风吹来,苞谷林中不时地发出喃喃细语,我似乎感觉它们这是在向月河致以谢意,它们这是在感谢月河用母亲般的乳汁,为它们注入了旺盛的生命力。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别了,美丽的月河,你总是这么静静地流着,流着,就如年轻的铁道兵战士,流血,流汗,不图回报,奉献青春,无怨无悔!别了,月河,我心中的女神,我不知今生是否还能回到你的身边,把这段难忘的青春再次回忆!这是1997年夏季我独自重返月河的回忆。文中所叙,皆是当时的真实场景 和内心感受的再现,因为岁月并不静好,所以才需要我们负重而行!据我所知, 后来去月河的战友和西安的学兵是越来越多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情不自禁地伏在钢轨上痛哭不已!他们这是在纪念那段己经逝去的青春年华,艰难而又充满激情的岁月总是令人怀念,值得珍藏!月河两岸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已不复我当年所见之情景了。我祝愿那里的人们生活越来越好,我祈愿美丽的月河再也不要像从前那样地忧伤。

车云华:原铁道兵11师53团,四川峨眉山市人,1970年12月入伍,铁道兵53团20连战士,担任车床工作。1975年3月退伍后分配到中国地质科学院三五一研究所机修车间工作,1977年3月调所政治处工作,1991年5月办理停薪留职手续后下海经商,2012年9月退休。
照片由作者提供
(本版编辑: 老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