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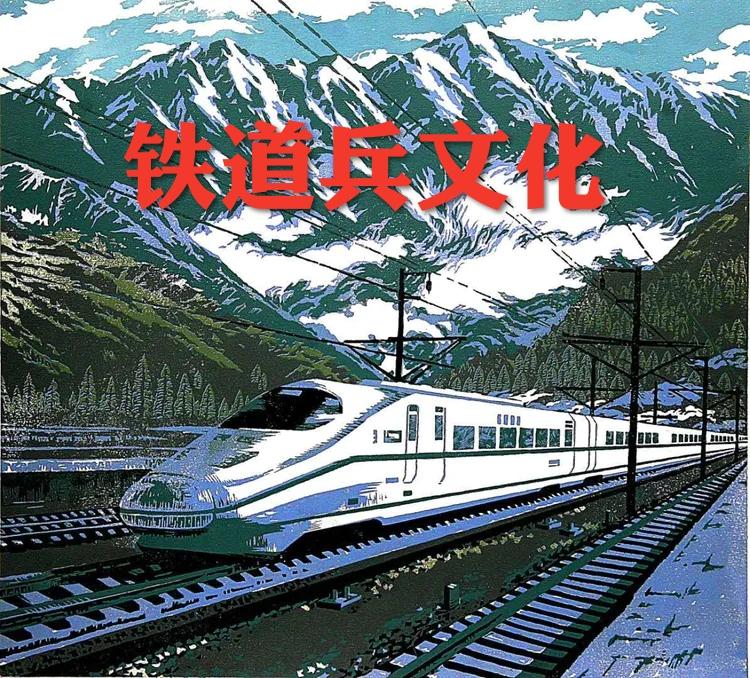
不知道怎么回事,自从12月16日被新冠阳了以后,尽管第二天高烧就从39.2℃退到38.5℃,以后每天陆续退烧,直到12月22日体温基本恢复正常。但是,期间没有食欲,加之于口苦,咳嗽,黄痰,心烦意乱,彻夜难眠,搞得人坐卧不宁,想写什么总是定不下心来,一样的东西,同样的时间可能会写二千多字,现在只能写一千多字,而且还感觉文思枯竭,不是那种文笔流畅,没有那种一气呵成的感觉。据专家说,这新冠不仅损坏心脏,肾脏,肺腑,还损坏人的大脑,影响人的思维,我这几天就感觉这个可恶的新冠已经对我的大脑思维造成影响了。但愿以后能慢慢地恢复吧!
衷心祈祷亲友们阴的不阳,阳了的早康。
(以下是正文):
在“抓革命促生产”的中央文件精神指导面前,城市工厂开始复工了,农村劳动生产也逐步恢复正常了。
最乱的地区学校也开始有了新的文件指示精神,叫“复课闹革命”。三年没有升学的我们突然听到这些消息,当然都十分高兴。最高兴的还是那些当家长的,孩子们有了学校可去,总比在村里游荡要好的多。不过西梁村学校开学会晚的多,因为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的那次武斗,把桌椅板凳全都砸得稀巴烂了。
这文革期间被耽误学业的学生称为“老三届”,也就是六六,六七,六八届毕业生。我们算是老三届小学生。因为初中的,高中的学生一直都没有毕业,我们小学也就没有学可升。现在好了,终于可以继续上学了。
最开始可以上学的是姐姐他们那一届的小学毕业的学生,也就是六七届的小学毕业生。可以不用考试直接升到初中,唯一的条件是必须是贫下中农成分。他们这一届上初中走了,我们才能上小学六年级。
六九年下半年,姐姐他们去安阳十三中学(后来改为二十五中)上学了,我非常羡慕他(她)们,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也去上中学呢?
十三中学位于安阳电厂附近,紧挨着柴库村,与我们村相隔三里地。那时候都没有自行车,中午学校也没有午饭。学生上下学每天都需要步行四个来回。
姐姐是一位十分勤快的女孩,早上在生产队干一早上农活儿,生产队记两个工分,匆匆忙忙吃口早饭,有时候早饭都顾不上吃,拿块干粮就直奔学校上课。学校当时是半天上课,半天劳动。即便上课,也是学工,学农,学军三结合的学习方法。课程除了一部分数学,语文,剩下的就是如何养猪,如何看人体穴位,如何当赤脚医生,如何防治庄稼病虫害等等。为此,姐姐很不感兴趣,经常抱怨,学习这些没有什么用处,还不如在家去砖厂劳动,多挣几个工分。同一个生产队的几个邻居女孩风云,平儿,宝云等都在砖厂拉车上土,也不少挣工分赚钱,她很想同她这些姐妹一起为家庭增加收入。
突然有一天,姐姐对我说,“兄弟,要不你替我去上中学吧!我给班主任刘风清老师说好了。”
“行啊”!我以为姐姐是随便说说而已。
谁知道,第二天,姐姐真的让我给她一起去中学报到。
见到班主任刘风清老师,他问了问我的年龄,我多报了一岁,刘老师只是说我个子不高,别的也没有再说什么。就这样,我顶替姐姐上了中学。

这上学容易,要想跟上课程却不容易。尽管学校学的是半天文化课,半天劳动课,但是,那些文化课毕竟我都没有学过。语文,学医,学养猪这些课都容易听懂,容易跟上课,唯独数学课是有知识连贯性的,要想跟上课,就必须补课学习。特别是分数这本数学六年级的课程,我根本没有学过。为此,我经常晚上到小学数学老师范厚用家里去求教,什么“通分,约分,最小公倍数等等”都是通过范厚用老师的补课才明白的。白天,在学校我经常请教范显君同学,他的腿虽然说有残疾,必须拄着双拐才能行走,但是他学习很刻苦,每天在学校带着干粮,吃点儿咸菜,喝点水凑合凑合,但是他从不耽误学习课程。无论刮风下雨,天冷路滑学习一如既往。我被他这种热爱学习的精神所感动,就经常求教与他,到交作业时候,也经常抄写他的作业,抄写过后再慢慢消化。就这样,慢慢地我基本上跟上了课程进展。
三年没有人升学,三年没有人入学,突然有两三届的学生都来入学了,教室,教具桌椅板凳都不够用了。学校发动全体学生自己动手烧砖砌墙,我们从外面拉来黄土,和好泥巴,装进坯斗,晾干以后再在烧砖师傅的指导下,烧制出成千上万块红砖,等到够一定数量,学校又请来专业泥工师傅,建造起来新的校舍。
校舍建起来了,这是我们学工的结果。学农支农方面,我们不仅每个排都有自己的学农基地,还及时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力的支援。记得有一次天气突变,冰雹灾害降临,学校附近的北士旺村、丰安村受灾严重,庄稼被冰雹打得稀烂,学校的全体师生自带干粮,自带救灾工具,水桶,铁锹之类,跑到受灾最严重的地方,补种红薯苗,第三天又跑到范家庄救灾救难,老百姓当然十分欢迎。可我们这些学生,却一无学成,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学校以及我们只能如此行动,并为自己的行动大唱赞歌。
说起那次抗雹就灾,有一件事情让我记忆犹新,难以忘记。
记得是去范家庄救灾,早上母亲给我烙了三张白面大饼,用作我中午的干粮。并一再嘱咐,这三张白面大饼,你一定要自己吃掉,不要同别人分着吃,一分,你可能就吃不饱了。结果,中午休息的时候,同学们都坐在一起说说笑笑吃干粮,我也拿出自己的白面大饼准备开饭。

和我坐在一起的有赵常庄的一位同学,我就客气地让了让他:“给!吃点儿大饼吧”。
谁知道他竟然一点儿也不客气,直接就把我的一整张白面大饼拿过去吃了起来。狼吞虎咽片刻功夫就把我的那张大饼吃完了。紧接着又掰了我半张饼,一边吃一边说,“这白面烙饼就是好吃”。 一边说一边把他自己带来的红薯面窝窝头让我吃。我赶快抓紧吃着剩下的烙饼,一边指着他的红薯面窝窝头一边对他说,“你吃吧,我不吃”。
后来才知道,赵常庄位于洹河北岸,属于丘陵地带,当时的条件在周边农村是很差劲的。家里平常很少有白面馒头可吃,更别说是吃白面大烙饼了。这位同学在范家庄救灾,看到我的白面烙饼,也是眼馋的不得了了,才不客气的吃了我的大饼。
我也是难得一次带这么好的干粮出来,虚伪客气地让了让他,谁知道竟然白白损失了一张半美味的大烙饼。其实我们家条件也并不是有多么多么好,仅仅比起赵常庄那位同学要稍微好点吧!不然,我也不会把这事记得这么深刻,这么久远了!
《乡村记忆十九:学生篇1》完
范顺成于2022年12月24日
多写几句话:许多读者可能会说,你就是一个小小老百姓,写这些有什么用?我告诉您,我写这些就是要告诉子孙后代,当年的社会就是这个这个样子。这才是原汁原味的基层社会的真实写照。不要相信电影和教科书。尤其是刚经历过的三年疫情,几百年才有一次,我也会如实写出来。不会歪曲,不会夸张,不会虚伪!
编辑:岁月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