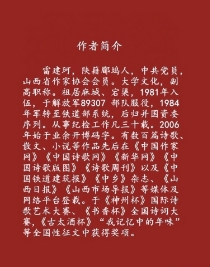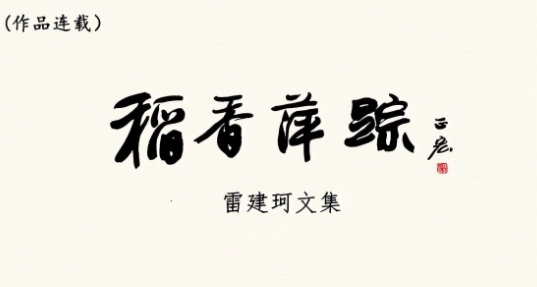干大及其他
前不久的川渝之行,中转的闲暇中,无意间看到一种植物,眼前随之一亮,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不禁勾起了隐匿心底几十年的一些记忆。
不硬气的“干大”
多人都有干大干妈,而我自小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干大干妈。说起来小的时候是有一门亲戚可以称其为干大干妈的,但却是不明不白蹭来的,并不真是自己的干大干妈。 按照老家河滩的传统,只有在家里排行老大的子女,才有资格拜寄一门干亲。 我上面有哥哥,哥哥有干大干妈,而我没有。这样,便按照约定俗成的所谓“规矩”和大人的要求,我和弟妹一起便跟着哥哥有了一门“干亲”。
“干大”其人
按照关中习俗,“拜干亲”一般在孩子出生“满月”的当天,由其祖母或祖父抱出去,出门后碰见的第一个成年人即拜为干大。当然,这种“碰” 除了有一定的随机性外,大多数场合往往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碰”见的第一人,或是与他家关系要好,或是有地位有身份之人。哥哥小时候拜干大是否有过事先安排已不得而知,但“干大干妈”和我们两家的关系向来非常好却是不争的事实。哥哥的干大也是本队人,乃上刘家院子叔辈,晚辈称其为“九叔”的,因其在族内同辈中排行为九而得名。“干大”祖上相传为汉中府褒城县七星棋麻雀湾书香大户,于清乾隆时迁居本村。“干大”中等个头,一副稍显清瘦的脸庞,留着灰色的胡茬,为人豁达宽厚,沉稳自敛。与世无争的微笑中,透着本分与和善,很容易接近。“干大”说一口绵柔地道的乡亲话,闲暇时,口里时常含着一支短小精致的烟袋锅,有滋有味地品吸着亲手在自留地里种出来的小兰花旱烟。遇有雨雪天无需下田的日子,“干大”便会从东边的上刘家院子,慢悠悠地踱到西边的干亲家串门。“干大”为人和善,深得家人爱戴。他也从不做作客气, 进了门便脱鞋上炕,斜倚在炕头和爹妈聊着闲话。一杯清茶,一锅旱烟, 和着一串家长里短、儿女情长的深情叙说,构成了一幅惬意自在的农家小院生活画。
说起“干大”,自然就有“干妈”的分儿。“干妈”名讳新珍,娘家是邻村积谷寺三队的陈家,祖上也是四川人。干妈的亲妹妹嫁到了一队黄家,属于婶婶辈,这位婶婶有个女儿叫海棠,文静聪颖,曾和我一起上过小学。“干妈” 是她们这一代人里为数不多的缠了小脚的女人。虽说干妈小时候缠过“小脚”,却缠得并不彻底,“干妈”有足够的自信承担队里的生产劳动。无论下地劳作还是操持家务,“干妈”都是一把好手。“干大”不拘小节,只负责出工,疏于家务。全凭了“干妈”精打细算和精心筹划,才让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大家庭过活得妥妥帖帖。“干妈”一生育有六子二女八个孩子, 个个知书达理,谦逊进取。
稀奇的“吃货”
说到“吃货”,就不免聊聊其含义。“吃货”是一个常用的口语化的俗语,在关中一带,其本意为好吃的零食。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物品极其匮乏,甚而吃饱肚子也成了一种奢望。哪个小孩子如果还有零食吃,那简直就是土豪。在此情形之下,可见“吃 货”对孩子们的诱惑有多大。如果孩子淘气,大人就会对孩子说 :“狗娃子不要淘气,妈明天去街上给娃买吃货呀”。就是再淘气的孩子,这时候也会服服帖帖了。对于平常人家的孩子来说,有吃货可吃实非小可,其兴奋度真不亚于过年,岂能因小失大。 还记得小时候跟着哥哥去“干大”家蹭亲戚的情形。

“干大”家所在的上刘家院子,方方正正,由大小十一户人家组成。“干大” 家位于院子的东南角,上房坐南面北,上房和东西厢房之间的空间,朝北面的大院中心方向自然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小院落。“干大”家的小院子总是收拾得平展清爽,这自然是“干妈”的功劳。家里除了聪明朴实的强哥、来哥、根哥和五哥外,还有热情端庄的巧姐和崴姐,并有两个小弟。二位姐姐冰雪聪明,颇具家姐风范。大姐巧凤嫁到了相邻的岐山安乐瓦房村,二姐崴凤嫁到了本镇高桥二队。“干大干妈”一家人最是热情好客,总是对我们关照有加,强哥还带着我们到过别有一番情趣的后院玩耍。 “干大”家的后院位于东厢房后面的空闲地带,一条水渠自南院墙处流进来,自南而北将长条形的后院一分为二,水渠往东到东院墙之间是密密匝匝的竹园,竹子挺拔粗壮,郁郁葱葱。水渠西边才是真正的后院地带,因为隔着水渠,小孩子们根本进不了竹园。水渠边上长着一丛丛有半人高的有 点像芦苇的绿色植物。植物根部有一些泛着深红色纹路的粗壮的芽孢。
强哥指着那些根部的红色芽孢,对我们介绍说是一种非常好吃的食物,叫做“洋火”,是客人从四川老家带过来的。当时便觉得十分新奇,这种“吃货” 怎么叫“洋火”呢,洋火不就是我们常用的点火用的火柴么,如何又变成了“吃货”呢,还有这种“洋火”究竟什么味道?带着这些疑问的我,很快便有的答案。吃饭的时间,饭桌上除了过年待客的拼盘肉菜之外,还真有一碟子凉拌的所谓“洋火”。强哥介绍过菜品后,我便迫不及待地夹起一片“洋火”吃了起来。感觉是用开水焯过后又凉拌而成的,酸甜爽口,风味的确有些特别。“洋火”味道的谜底算是解开了,而“洋火”这一名字的谜团却始终藏在心底无以释怀。再则,此后因为无缘再次得见所谓“洋 火”这种吃货,也便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将其渐渐淡忘。 直到五十年后的前年春节,携妻、子去重庆旅游时,竟然在位于鹅岭附近的一家菜市场内再次发现了“洋火”的踪迹。当时是早已将其名字遗忘到爪哇国去了。便用熟练的重庆话询问摊主,其名若何时,得到的竟然还是记忆深处隐藏着的“洋火”。随之便当即用手机上网查询,却原来是 “阳藿”两字。
“洋火”之谜
经查阅网络,百度百科对“阳藿”这一词条的解释为 :植物学名 :蘘 荷,是一种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从它的地下茎发出的露出地表的花蕾可以食用,也称之为“蘘荷”,是一种香辛蔬菜。分布于江苏、湖北、四川 等地。阳藿富含多种氨基酸、蛋白质和纤维素,嫩根茎含 α- 蒎烯、β蒎烯、β- 水芹烯等物质。是风靡日本市场的抗癌保健野生蔬菜 ;根茎可入药,“性温,味辛淡,忌铁”,具有活血调经、镇咳祛痰、消肿解毒、消积健胃等功效,可治疗便秘,糖尿病等病症,素有“亚洲人参”之美誉。

据《本草纲目》记载,阳藿不仅可作为蔬菜食用,有活血调经、镇咳 祛痰、消肿解毒、消积健胃等功效,对治疗便秘、糖尿病有特效,具有较 高的药用价值。阳藿含有多种氨基酸、蛋白质和丰富的纤维素,所含纤维素还是一种不产生热能的多糖营养物质,经常食用,有利于保持消化道通 畅,维持正常的排便功能,可治疗便秘,消积健胃,对于糖尿病有特殊功效。因此,阳藿是一种食药兼用的纯天然膳食纤维食品。

阳藿的食用,以刚出土的紫色或粉红色幼嫩芽苞(实为花苞)为上佳, 其花苞非常美观,红红的形如竹笋。食用方法 :一是凉拌,洗净后用开水焯至半熟或在火上烤至半熟,加盐或酱油、味精等拌匀 ;二是炒食,与肉炒或单纯炒食之,四川某些地区如皇木古镇则用阳藿炒腊肉 ;三是泡腌, 制成泡菜或腌菜,其色泽美观、风味独特,香味浓郁,令人回味无穷。
既有百度为证,可见“阳藿”这一当年的稀奇吃货,实为生长于中南地区的一种常见的特色蔬菜。还有《本草纲目》对其活血化瘀,治疗糖尿 病等之释义,加之日本对该植物之抗癌功效多有推崇,且素有“亚洲人参” 之美誉,可见“阳藿”确实为一种值得推广运用,对大众保健养生极有裨 益的真正的“吃货”。
2019 年3月16日 惠远
草 鞋
偶尔之间叙及草鞋,不经意中便勾起了深藏于脑际,那一段久远的记忆。

小时候,爷爷打草鞋是一件冬天农闲时的寻常活路。那时候资源匮乏,三毛钱一双的手工草鞋可以穿上几个月,尤其老家西河滩一带,临近秦岭大山,大冬天里需要赶山的人们,对精致耐用的手工草鞋尤其情有独钟。 那时候经常可以看到用裹腿或毛练(一种用羊毛制成的绵裹腿)缠裹了腿 肚,穿了草鞋的精壮劳力背着硬柴或各种山货从斜峪关口出来。气力实在不支的就在关口的供销社收购点发货(指以比市场便宜的批发价把货物交售给公家单位的交易方式),稍微有些后劲的便再咬咬牙关,继续背了几百斤重的山货,沿着眉斜公路,一口气再走上 13 里下坡路,便可到达人气兴 旺,更热闹的齐家寨卖上个好价钱。这些人每天成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赶山路,凭的便是脚上那双既厚实又合脚的手工草鞋。这些体力非凡的汉子们,每每将自己辛劳所得换得可怜而有限的一些钞票后,除了饱餐一顿,给家里买些生活必需品外,最重要的就是在固定不变的草鞋市上,再买上大几双成十双的手工草鞋回去,为下一阶段的赶山做准备。就是十里八村的庄稼人们,家里劳力少、家境差些的,在脚上蹬一双手工草鞋的也并不罕见。我刚上学不久的那些年,在我们这些十岁上下的孩子们中间,流行 一种机制草鞋,由供销社代销,比手工的草鞋要轻巧洋气得多,以至于许多同学都不愿意穿自己妈妈做的硬而磨脚的千层底布鞋,争相购买了这种一毛八分钱一双,俗称“二里半”的草鞋,一时间,竟成了一种时尚。记得我也曾抵不住诱惑,缠着父亲用两颗鸡蛋从村里的“双代(代购代销) 店”换了一双“二里半”回来,穿在脚上很是神气了几天。

与机制的“二里半”不同,手工草鞋制作起来十分费功夫。主要原料就是稻草,家里就种水稻,草自然多的是,应有尽有,毫不费力,只需挑选上等的好稻草,刷掉多余的护叶,喷上适量的水分,放置一段时间,使其变得柔软待用。麻烦的是作为草鞋经脉的一种东西,称之为“练”的, 这是一种采自深山老林生长的叫椴树的第二层皮制成的。椴树皮分两种,专用于作“练”的,须取自成年椴树紧贴树干木质那层柔软而有韧性的薄皮才行,是为“椴皮”,椴皮再干也不会断裂。从深山老林里刳回来的椴皮须仔细加工成所需的粗细匀称的条子,再由把式扎制成不同尺寸的 “练”,然后风干备用。

最早的时候家里大多由爷爷打草鞋,奶奶只是做做帮手,后来爷爷年老体衰,奶奶便接着织了几年。记得在家里院子靠西北角的那间不算大的草房里,先由奶奶把早已风干变硬的所谓“练”在水桶里泡发得十分柔软时,递给已坐在草鞋板(一种宽而长的木板,可以骑在上面作为工作台的板子)上的爷爷,然后由爷爷上练织打草鞋。面前,板子的另一端挂着草鞋耙子。所谓草鞋耙子,就是在一段横的原木上朝上并排钉六个去了盖的 中等的土钉,用来固定和挂住用于做草鞋经线的四根所谓“练”,在耙的中间部位平着凿一卯孔,嵌入一截约一尺长,顶端有勾的木棍,以便能从下边钩住草鞋板的顶端,从而起固定作用。“练”的外端分作四股挂在草鞋耙上,靠身体的一端便挂在腰间的特制腰带上。一只草鞋的工程便开始了。爷爷戴着一顶圆顶草紫色的那种有一对绒扇的棉帽,黑色的对襟棉袄上系了腰带,弓着腰坐在草鞋板上,一双布满老茧、粗大而有力的手一边沉着地搓着稻草,一边自如调整着“练”的间隙,不到两个时辰, 一只精致美观的草鞋便织成了。一天下来总能织上两双的样子。草鞋板下边是一小盆木炭火,用以驱赶严冬的寒冷。这里也是我儿时的欢乐园。因为有爷爷的慈爱,有那盆木炭火的温暖,围着爷爷和草鞋板玩一会,一双冻得像红萝卜的小手,便赶紧滚在火盆边上烤一会,其中简单的快乐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暖融融的。

记得那时周日逢集,头天晚上爷爷是不得睡觉的。他须用一晚上的功 夫来对那一大堆草鞋作最后的加工,使它们看起来美观,穿起来光滑可脚。 第一步,他用剪刀把草鞋表面露出来的草头清理干净,其次,在各连接部 位穿好用于系扎的椴绳,最后就是用硫磺把草鞋熏蒸得洁白无瑕。熏蒸草 鞋是十分讲究的,在一只大瓷盆的底部中央置一只生铁浇铸的专用的硫磺 灯,比幼儿用的小碗略小,却质地极厚,放入一只板栗大小的黄绿相间的 硫磺块,点着后,就有一星若有若无的蓝色的火苗在慢慢攒动着。紧接着, 一股带了一丝香味却又呛人的硫磺烟的味道就在屋子里弥漫开来,我们随即便跑开了,而爷爷似乎并不在意,也不咳嗽,而是不紧不慢把那一堆修整好的草鞋结结实实一层一层棚在大瓷盆上,任由硫磺燃烧时散发出来的烟气,把那一双双草鞋直熏得一色的白净。这道工序往往需要一夜的时间, 那一小块硫磺的燃烧也会持续到次日早上。第二天一早,爷爷满肩前后挂了几天来辛苦劳作的果实,徒步到八里远的镇子南门口的集市上出售。

我还记得跟着爷爷去街上的情景。爷爷在不停地招呼买主,讨价还价,也和伙伴及熟人闲聊,我就独自在一边的石墙边玩。有时候,不大一会儿爷爷的草鞋便卖完了,草鞋行情好的时候每双可卖到三毛五分钱,一般情况也可卖到三毛多。卖完草鞋,爷爷便会先在旁边买一些带了壳的花生, 除了抓几颗给我吃外,其余的统统在腰间的一只很厚的粗布袋内装好,以便带回去给家里所有的人尝一尝。当时家里就是一个和妈同岁,患有驼背的小姑、大我几岁的哥哥和三弟,那时好像还没有四弟。装好花生,爷爷总会拖了我的手,从南街径直走到北街口的国营食堂花两毛五分钱买一碗带汤的羊肉来,爷孙俩一起享用。这是我记忆里,童年时光中最奢侈、最体面的乐趣了。有的时候,一大串草鞋在那里挂了一整天,也没人过问,更没有人买。

我一个小孩子,早玩得腻烦了,就会独自蹲在那堵不算高的石墙边打起盹来,爷爷怕我冻坏,总会不时喊我醒来。眼看着天就要黑了,总不能把这些等着换钱的草鞋又背回家吧,这时,唯一的办法便是把这些草鞋以较低的价格统统“发”给隔壁的供销社了事,而“发”给 供销社的代价,每双草鞋仅可得到两毛三分钱,却也别无他法,只好如此了。羊肉汤自然还是有的,只是等了这一整天。
2012 年冬 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