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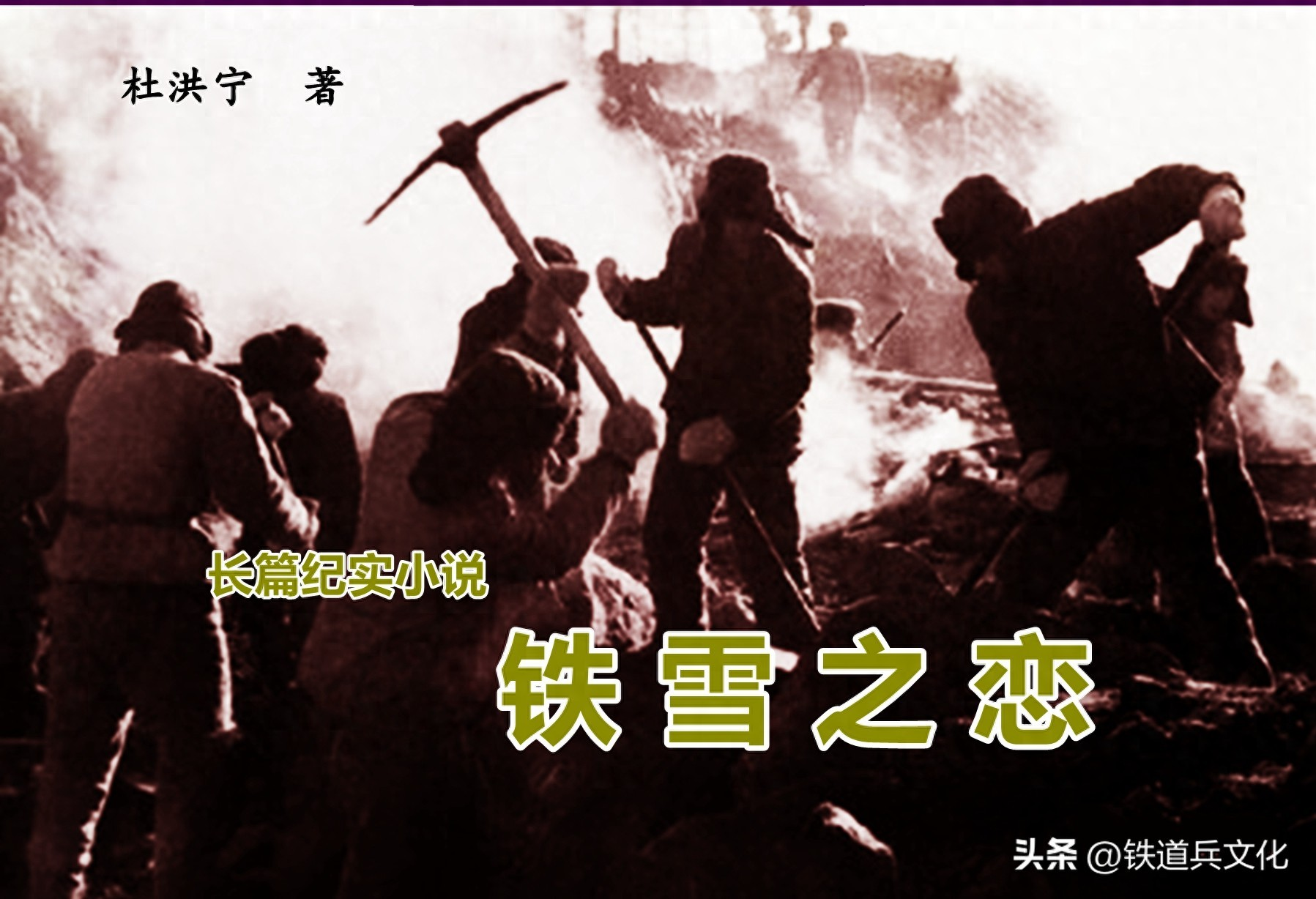
第五章 阿拉沟之春
明天,战友们就要分别奔赴不同的战斗岗位了,大家都收拾好了行装,做好了准备。今天,阳光灿烂,部队特意放了假,还请来了托克逊照相馆的摄影师为大家拍照留念,大家都非常高兴,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八连一班的全体战士自然少不了拍一张 “大团结” 合影,记录下这难忘的时刻。然后,大家又三三两两地分别拍单人照、三人照等等,想要把这珍贵的瞬间永远定格。拍完照,大家纷纷结伴去附近看风景,或者跑到县城里逛逛,享受这难得的闲暇时光。
大家都得到了确切的分配通知:聂冬青,毛少龙,张君还有丁铁军的室友 ——“快乐的理发师” 孙志伟被分配到了汽车连,这可是个非常了不起、人人羡慕的岗位,因为在汽车连可以学到开车的技能,将来到了地方也能靠这门手艺挣钱养家;罗班长带走了刘建、李明林、李光能、等他们被分到了施工第一线,最能攻坚克难的猛虎连队,分到猛虎连的人心里都有些忐忑,因为那里可能是最危险、最能考验人的地方,原来罗颜红班长就是猛虎连队培养出来的干部苗子,怪不得八连一班的成绩会那么出色;余下的丁铁军、梅松、白成昆、张四果被调到了师部政治部文艺演出队,分到演出队的人最惹眼,因为这代表着未来的生活可能会特别靓丽精彩。
这一分配结果,自然就把八连一班分成了三队人马。大家心照不宣,不约而同地照了三张小合照。这三张照片,不仅划定了一班同志们军旅生活的范围,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人生发展的方向。女兵连中,顾银燕、白雪、朱巧芝也被分配到了演出队,姚淑娟则被分配到了部队医院。
照完相,丁铁军和聂冬青没有去别处,两人在寝室里低头写着信。他们除了给家里写信,汇报自己的近况,就是给还在农村的好友史露露和袁小丽写信,告诉她们自己分配到部队具体单位的消息。给家里的信基本上是每个月一两封,而写给这两位女农友的信则比较频繁,一个星期就有一两封,她们的回信也很及时,一对一地交流着。现在,两人的挎包里已经积攒了厚厚的一叠信件。
在信里,他们把新兵训练过程中的各种情况,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都如实汇报过去,每天都沉浸在期盼收信、看信和回信的快乐之中。每次写信,丁铁军和聂冬青都是分别写给史露露和袁小丽,信的内容也会有些小小的区别,而史露露和袁小丽的回信也是如此。或许,这两个女孩子会互相看彼此的信,但丁铁军和聂冬青却从不互相看对方的信,只是偶尔会坐在一起,各写各的,享受这份宁静而美好的时光。这个奇怪的现象一直维持了很久,直到三年后聂冬青探家才结束。
接下来,晚上的大聚餐开始了,这顿散伙饭格外丰盛,还可以随便喝酒。丁铁军和聂冬青在农村时就会喝酒,面对这么好的酒,自然少不了尽情豪饮。其他的人,不管能喝的还是不能喝的,都端着酒杯,相互敬酒,诉说着离别的不舍与祝福。大家在一起相处了几个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彼此都非常留恋,舍不得分开。很多人喝得眼泪汪汪,有的笑,有的哭,有的相互紧紧拥抱在一起,死活不愿意分离。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次分别后,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再也见不着了。
当晚,或许谁都很难入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海里想了很多很多。直到快天亮时,才渐渐睡去。在梦中,一首不知名的歌谣萦绕在耳边,仿佛回响在天界:
在那高高的雪山云中之颠,
有雄鹰在空中久久盘旋。
在那山峰中间的山沟,
是曾经的我们的家园。
一座直直的木桥,
连接礼堂和军营小院。
红柳生长在两面,
石头堆积成围栏。
伴在一路欢唱的小溪边……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数十万仁人志士响应祖国的号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远离城市、四面环山、荆棘茅草遍地的阿拉沟。他们用青春、汗水、热血甚至生命,在这里建设起了一批规模化的军工企业。英勇无畏的铁道兵指战员们不计艰险,浴血奋战,修建了工程浩大的南疆铁路,并配套建设了电厂、医院、学校、电视台等设施,让阿拉沟变成了一个美丽的世外桃源。
阿拉沟位于新疆南天山之中,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大山沟,地势十分险恶,最窄处仅能通车,真可谓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阿拉沟还是古丝绸之路的 “天山道”,一座历经千年风雨沧桑的石垒烽火台矗立在阿拉沟口,见证着岁月的变迁。
阿拉沟又称 “四季沟”,因为从阿拉沟口一路上行到奎先达坂,仅几十公里的路程,却能让人领略到春、夏、秋、冬四季的风光,十分奇妙。1975 年 10 月 15 日,中央军委电令铁道兵东北指挥部调驻新疆,改称铁道兵第二指挥部(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 89112 部队),铁二指机关就驻扎在天山阿拉沟,主要承担南疆铁路修建的指挥任务。
南疆铁路是新疆南部的主要铁路干线,铁路走向大致沿古 “丝绸之路” 的中路延伸。沿线的地质、地貌、气候条件十分复杂,有高达 45 度的高温戈壁沙漠,有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冰大坂,还有常年刮着七八级强风的大风口。吐库段全线一半以上地段穿行于天山峡谷,共修建隧道 30 座,架设桥梁 463 座,隧道总长度达 33 公里。
南疆铁路从海拔 800 米高升至 3000 多米,再降低为 1200 米,形成了最大坡度为千分之二十二、长二百四十多公里的连续大坡道,这在中国铁路建设史上是极为少见的。其中,咽喉地区的奎先隧道建筑在海拔三千多米的冰达坂上,长 6152 米,是中国海拔最高、最长的隧道之一,修建难度极大。
罗颜红带着罗世杰和战友们乘坐的大货车,在路上走了两天。第一天,车子在戈壁沙滩上风驰电掣,晚上就住在阿拉沟口的车上。第二天一早,车子从沟口沿着山沟一直往上爬行。沟口已经是春意盎然,五颜六色的野花在路边竞相开放,散发着阵阵清香。随着车子不断上行,季节和景色也在悄然变化,他们经过了很多部队驻地,还有医院、工厂等等。到了中午,周围已经是高原风光,看得见远处的雪山和广阔的草原,还有悠闲的牛羊在草地上吃草,湛蓝的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美丽极了。
下午傍晚时分,车子终于到达了白雪皑皑的奎先达坂,接近山顶的山腰处,这里就是猛虎连的驻地。一排排营房在风雪中矗立,显得格外坚毅。奎先隧道的洞口就在连队驻地下方几百米处,像一头巨兽张开的嘴巴,等待着战士们去征服。
到了这里,没有丝毫犹豫和彷徨的余地,所有人都立刻投入到工作中,一边学习施工技能,一边参与实践施工。罗颜红班长已经被提拔为副排长,他亲自带领新兵们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任务非常紧急,大家必须努力工作,才能完成每天的工作计划。
新兵们首先面临的是生活上的艰难。达坂上依然是严冬的气候,气温都在零下几十度,寒冷刺骨。由于海拔高,气压低,馒头是蒸不熟的,饭也是半夹生的,难以下咽。菜是压缩菜,吃起来有点像猪草的气味,让人难以下咽。炊事班的战士们想尽了千方百计为大家改善伙食,可是收效甚微。后来,顾银燕根据这种情况,创作了一个舞蹈叫《风雪高原炊事兵》,生动地展现了炊事兵们的艰辛与奉献。
小小的营房里,一个班住一间。每天要轮流留一个人在家,打扫卫生,整理内务,还要和另一个班的人合伙去抬水。那些水是从山下用水罐车拉上来的,每班只能分到一大桶,分到每个人头上,就只有一脸盆水。这盆水,无论是洗脸、漱口、擦身子,都得省着用,更别说像在家里那样畅快地洗澡了。
走出营房,放眼望去,除了雪山、云雾、小路和石头,没有任何的商业设施和娱乐场所,也没有街道、小巷,更看不到姑娘的身影。除了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几乎看不到任何的人烟,生活单调而枯燥。
然后是工作的艰难。每天,大家穿上厚重的工作服和长靴,沿着崎岖的小路往隧道洞口走。那里的风很急很狂,而且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吹,往山顶方向一个劲地猛吹。下山的时候,要硬着头皮跟风对着干,风大的时候就停下来,风小的时候再继续走,一步一步,十分艰难。而下班回来时,却很 “魔幻”,根本不用自己费力走,风会像推着风帆小船一样,把人轻松地推上山,还伴随着一种特别的 “音乐”—— 那是在隧道里打湿的棉衣和裤子,早就被冻僵成了冰块,在运动中发出哗哗的响声,而且很容易就被磨破了。
进了营房后,大家先是站在原地喘口气,然后坐在床边,自己根本脱不下冻得硬邦邦的靴子,必须得战友帮忙,你帮我,我帮你,才能比较顺利地脱下衣服和靴子。之后,用自己那宝贵的一点水源简单擦洗一下身体,完了就躺在床上,继续喘气,缓解一天的疲惫。
夏天的时候还好些,到了冬天,日子就更难熬了。生命的维系全靠营房里的火墙,如果煤炭质量不好,火炉歇火,那么第二天,人可能就会变成 “冰冻睡美人”,冻得起不了身,出不了门。所以,那煤炭就是黑金,是无价的生命之源,必须早早储备好。罗副排长最关心他们这几个新兵,他对连队司务长很有意见,愤怒地指责司务长欺负新兵,把不好的煤渣都分给什么都不懂的他们。这几个新兵是他亲自带的,为了能让他们平安度过严冬,他必须想办法帮忙。凭借他的老经验和能力,他甚至不惜违反纪律。
有一天,天降大雪,那雪花大得像巴掌一样往下砸,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白茫茫之中,人显得被装在棉花桶里一样视线孤独而狭窄。温热的人体在这冰冷巨大的白色冰桶包裹中,是那么的渺小微弱。就在这样的天气里,罗副排长带却领着他们去“偷”煤炭。大家两人一组,带着一根扁担、一条麻袋和一根绳子,手牵着手,脚跟着脚,在厚厚的积雪中摸索着前进,有时甚至需要爬着走。大概走了一千多米的距离,感觉像是走了一个漫长的冬季,才终于摸到了连队锅炉房的煤炭存放场。
他们只挑着大块的 “黑金” 往麻袋里装,然后抬着一袋又一袋往营房搬,来来回回弄了好几个回合,累得半死。汗水、鼻涕、唾沫混在一起,在脸上结成了冰碴,脸上的五官仿佛都在相互 “扯皮”,又疼又痒。这场景,让大家又累又苦,欲哭无泪,却又隐隐感觉很刺激、很好玩。平生第一次偷东西,而且是偷自家的东西,这奇妙的一天,那偷东西的 “快乐”,那漫天的大雪和沉重的煤炭,那难以忘却的黑与白的记忆,一直深深感动着大家,直到今天。
隧道掘进的工作任务是按厘米计算的,每天能掘进两米,都算是奇迹了。六千多米的隧道,他们已经推进到了一千多米处。那施工的掌子面十分凌乱,到处是石头,到处淹着水,电线在黑暗中闪着火花,通风大管道发出呜呜的嘶叫声,风枪轰鸣着,装载车哇哇作响。在这样的环境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塌方掉石头的危险,随时可能出现缺氧、断电的情况。被石头砸到脚,被工具弄伤手,这些小伤小痛是家常便饭,甚至掉脑袋牺牲的事都有可能随时发生。仅仅几个月下来,他们就亲眼见证了战友的牺牲和负伤,深刻体会到了这份工作的危险性。
一开始,他们干的是装车、推车的活,刘健和李明林人高手长,干这活很有优势。后来,他们学会了点炮、放炮,李光能和另一个战友最适合干这个,因为他们个子小,动作灵活,跑得飞快,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撤离到安全地带。罗世杰打风枪最厉害,这活既苦又累,还很有技术含量,需要很大的力气和技巧。
有好几次,因为隧道内缺氧,罗世杰都昏了过去,大家赶紧把他抬到空气好点的地方,等他清醒过来后,稍微休息一下,又继续投入工作,没有丝毫退缩。
还有一次,他们遭遇了透水的地段。罗副排长经验丰富,听到声音不对,赶紧呼喊大家撤离。刘建动作慢了一点,没跑赢,被一团稀泥砸到头盔上,一下子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罗副排长见状,说时迟那时快,冲过去一把扯着刘建的一只脚就往外拉,所幸,后面又砸下来的大片稀泥石头被他们躲了过去,刘建才幸免于难。
然而,二排的一个新兵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就在那片透水的地段,在他当班的夜里,不幸被活活掩埋了。全连上下都陷入了沉默,谁也吃不下饭。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把战友的遗体抬上山,那里有一个墓地,已经安眠着一个班的战士。通过这次战友的牺牲,大家知道了一件事:牺牲后,会有 350 元的抚恤金,会连同奖状一起寄给家乡的亲人。这 350 元,在当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却也无法弥补失去亲人的痛苦。
不知不觉中,在这没日没夜、艰苦而又危险的工作中,时间悄然流逝,转眼就到了年底,更加寒冷的冬天真的来了。罗副排长因为工作出色,被提干当了一排排长,罗世杰也当上了一班副班长。其他的人,也都成了老兵,成了技术骨干,能够熟练地应对各种工作难题。
一开始,大家还经常给新兵连的同志们写信,分享彼此的生活和工作。可后来,随着工作越来越忙,联系也变得越来越少了。只有丁铁军和聂冬青还和罗排长保持着联系。不久后,有一个特大好消息传来:政治部文艺演出队近期会来连队慰问演出,聂冬青的车子会送他们来。到那时候,大家就能见面了,这个消息让所有人都兴奋不已,充满了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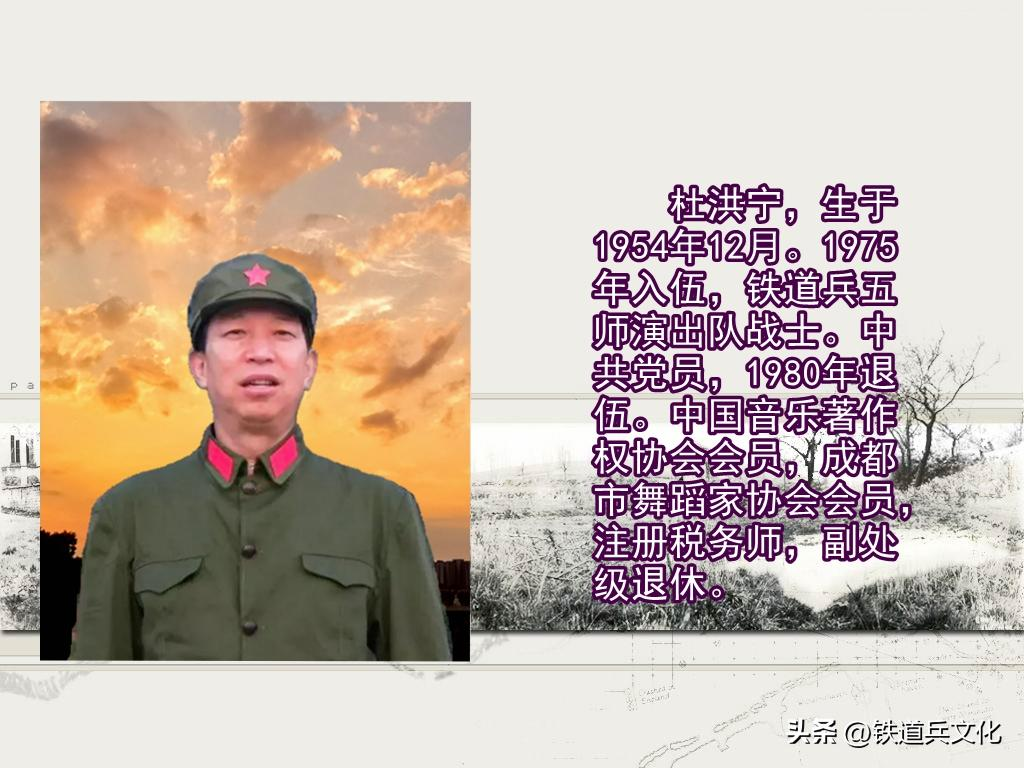
编辑:兵心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