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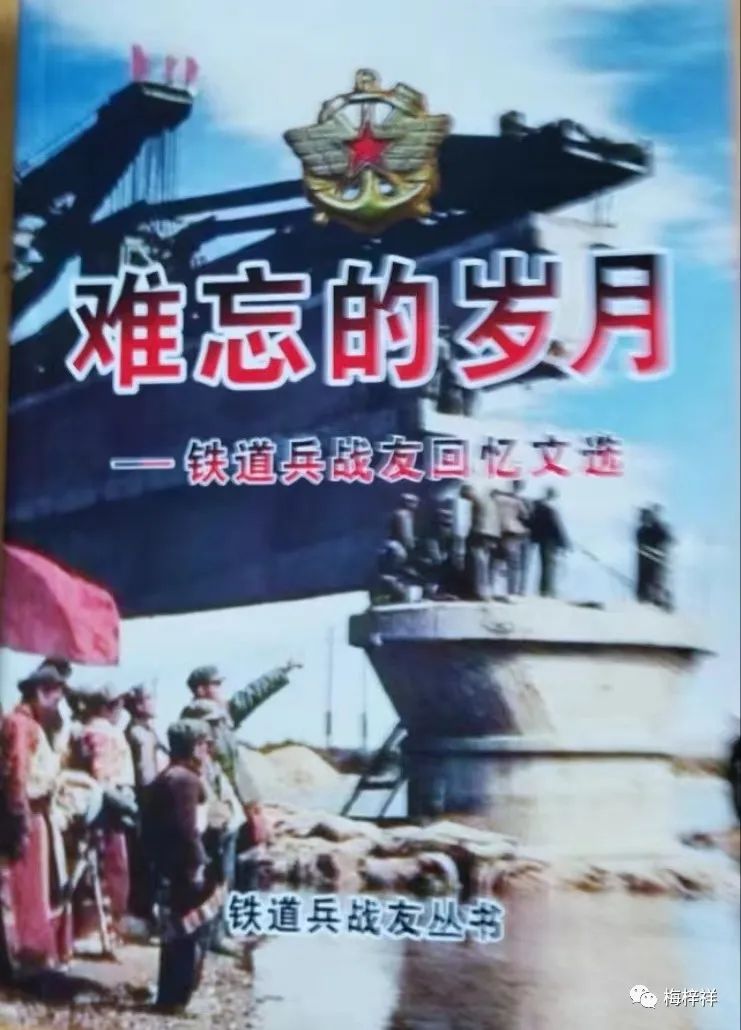
李康平战友是铁道兵的英才,在写作上有成就,出版过长篇报告文学《风雪新天路》等著作,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服役铁道兵部队的战友,加入中国作协的不会超过2位数。可见,“铁道兵作家”,是万里挑一的人。
写铁道兵打隧道、架桥梁的作品多,这是铁道兵的“主业”。李康平《军营往事的回忆》写他在仓库连当搬运工,在团业余宣传队当演员。这两项工作,当过铁道兵的人都比较羡慕,至少没有一线施工安全之担忧。读过文章,知道在铁道兵干哪一行都不容易。
铁道兵部队是一盘棋,每个棋子都重要;每个工种,无不是施工生产的必需。汗流浃背,是劳动艰辛的情状;李康平创造一个词“汗流浃腿”。仓库战士装卸工程材料,全身湿透,令人心疼的战斗生活。
那个年代,广播电视少,部队在穷乡僻壤施工,文娱活动缺乏。相当长时间,铁道兵各级机关有文工团、宣传队的编制。以现在的标准,当时的节目难登大雅之堂,但战士编、战士演、演战士,鼓舞士气,演出深受基层官兵欢迎,对完成各项任务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李康平回忆宣传队练功“压腿”“下腰”,以相声形式传播防冻知识,体现了文艺战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爱岗敬业精神。宣传队是铁道兵值得赞扬的一个群体,很多战友晚年撰写军营生活作品,还会深情回忆自己看过的一次演出、一场晚会。
军营往事的回忆
李康平
在53团几年锻炼成长经历,令我们铁道兵战友难舍难忘, 不禁又回想起70年代军营文艺生活。
当时,我在仓库连服役,在去团宣传队之前,我在仓库连经历了部队转战河北的搬家装卸。从宣传队回仓库,又遇上了部队到河北之后的安置装卸,一前一后正是仓库连装卸最为繁忙、艰苦的两段时间,恰好都让我赶上了。我觉得这似乎是一种天意,有意采用这样一种艰辛来锻炼我的体魄、磨练我的意志、培育我的品格,后来再看这一艰巨考验对我的确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以至影响到我整个人生。
在安康五里铺那段时间搬家装卸,每隔两三分钟就来一辆车,装卸1排和2排6个班轮番上阵。记得当时仓库连一台装卸机、叉车都没有(如果有的话,就该有个机械排或机械班了),装卸全是人工。装卸最多的是桥墩施工灌注钢筋混凝土拆下来的钢模板,每块三四十斤,每次搬一块。放下的时候不能因为模板重,从车上搬下来就往码垛上扔,那样撞击容易导致模板变形,影响再次使用。我们都是要用力搬起,轻轻放下,码放整齐。装卸是个重体力活,那段时间,我们整天都不能用“汗流浃背”来描述,而是“汗流浃腿”,因为不光是汗水湿透脊背,还常常是两个裤腿都汗湿透了。
我们新兵只知道努力干活,还是老兵潇洒,知道劳逸结合。为改善连队伙食,炊事班养了几头猪,仓库连轮流组织各班打猪草。仓库连所在的五里铺是一片川地,周边连接稻田和池塘的沟渠很多,里面长有一种水草可以喂猪,我们就挽起裤腿到水里捞水草。湖南、江西、福建等南方的老兵有经验,会在稻田和池塘边上抓泥鳅和黄鳝,抓回来洗净,破开肠肚,再摘些营房周边自种的辣椒,用一尺多直径的军用大铝盆当锅,架在三块石头上当灶,捡些木头烧火,炒了改善伙食。副排长石有才、班长马头元经常这样开小灶,看到一旁新兵来了,热情地招呼一起吃。我们当然不好意思,多半都是推辞,偶尔也尝尝,哪敢跟老兵平起平坐一起大吃!

图片选自网络。
从宣传队回到仓库连时,仓库连已经从陕西省安康县五里区移防到河北省滦平县虎什哈公社的岗子村,左边是汽车连,右边是去一中队和团部方向,隔一道河沟对面是3营营部。这时装卸多半都是打隧道做支护用的木头,还有粮食、水泥等物资。装卸木头两个人扛一根,我仗着个子高、力气大,总是挑大头扛,把小头让给个子矮的战友;水泥一袋100斤,我一般都一次扛2袋,最多时一次扛3袋,好在装卸不用走很远的路,几十米就卸下来了,还能挺得住。装卸粮食一麻袋有300多斤,我从高度正合适的解放牌汽车上一次能抱一麻袋卸下车来。现在回忆起来,仍然不是自己当时有多么高的觉悟,只是有种朴素的感情和自发的动力在支撑着自己,仗着自己个子高、力气大,也有种年轻逞能的意味。然而,我的这种“自虐式”苦干实干拼命干的表现,让时任仓库主任林良苏、指导员彭寿松、排长黄上松、排副石有才等领导都看在眼里。他们当年是怎么评价我的,我不知道,但是有一天彭指导员找我谈话,肯定了我的表现,然后给我一张入党志愿书,让我经受组织上的考验。
我是1974年3月16日经仓库连党支部党员大会讨论,接受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正式党员。石有才和另一个山东籍姓陈的副排长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那时入党没有预备期。我入伍才一年三个月,在新兵连三个月,在宣传队半年,在仓库连只干了半年,就被接收入党,这在同年入伍的战士中最早的。入党之后再有装卸任务的时候,我用力已经不再含有逞能的意味了,而是时刻意识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耳边常响起在宣传队经常哼唱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经典唱段:“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专拣重担挑在肩。”
部队转战河北沙通线,53团团部驻在滦平县虎什哈公社所在地,虎什哈当时有一条不长的小街,团部营房建在街的最外围。团宣传队的营房在团部和2营之间的潮河河滩上,坐北朝南的两栋平房。男兵在左侧的几间房,队部和女兵在右侧的几间房。房前是一块平地,用来每天练功、排练。大部队这时在滦平虎什哈境内,配属部队施工的地方民兵连也都组建进驻,施工会战相继展开。
宣传队接到的任务就是为施工连队和民工慰问演出。演出的节目都是宣传队已经多次演出的成熟节目,有黄德才等4人表演的口技,模仿越南战场抗击侵略者的飞机声、枪炮声、火车奔驰声、养殖场鸡鸭牛羊鸣叫声等,有声有色,惟妙惟肖;有周秀培的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是当年名曲,百听不厌;何杰凡的黑管与沈雄瑞的小号合奏幽默诙谐,常常令台下大笑;张英、包建瑛几个女战士与解向林合演的西藏歌舞《洗衣歌》载歌载舞,当年最为流行,至今也还有传唱。那段时间,宣传队下连队演出,几乎走遍了全团4个营和直属的所有连队,尤其正值冬天,女战士跳舞的时候还要穿着单薄的演出服照常上台,谢幕后立刻紧紧裹上棉大衣、抱一个装满热水的军用水壶蹲在一旁瑟瑟发抖。轮到下一个节目登台时,甩掉大衣立刻又精神抖擞起来。这些节目都是宣传队的保留节目,宣传队的老队友舞台经验丰富,演出配合默契,几乎不用走台、不用彩排,排上节目单上台就能演,赢得战士们雷鸣般掌声。保留节目单里没有,也不会有新来的我和小童的节目,那我们来宣传队干什么?这是个问题,我在思考。高队长跟我说,别着急,先学习,慢慢来。老队友们对我和小童也都非常友善,我们不会的,问老队友任何人,都热心地教我们。没节目演出,我们就搬运乐器道具、装台卸台多干点体力活,可是老队友们也都争着干在前面。在我们面前,他们谁都不把自己当大腕、台柱子的摆谱。我还在继续思考:在宣传队我还能干什么?机会总是给予有准备之人。没有留给我的演出机会,我就自己创造个演出机会。这时,从团部发下来一个防冻的宣传材料,由于部队刚从南方的陕南转战到北方的河北,又正值寒冷冬季,许多战士不懂防冻保暖知识,出现了冻伤。因此团部要求我们在文艺演出中加进一些防冻宣传内容。我认真地看了防冻宣传材料,自告奋勇承担节目创作的任务。我写了一段相声,创作之前,我认真分析“解剖”了马季说猪全身都是宝的一个相声,运用马季相声的手法来写防冻知识。相声只两三天就创作出来了,吴耀给予了重要指导,稿子就在高队长那里通过了。高队长说,相声是你写的,那就你来说,不光是词熟,自己的创作意图也熟。于是,我写的这段关于防冻的相声,就让我说逗哏,班长黄德才说捧哏,演出效果竟然出乎意料之外地好。我还是缺乏演出经验,说到要抖包袱的地方,自己都忍不住笑场了,台下更是笑声一片。只可惜当年我第一次涉足文艺创作的文本没能保留下来。

图片选自网络。
宣传队晚上演出,白天还照常要出操,毕竟是部队、是军人,这是一点也不含糊的。只是宣传队出操不像连队出操跑步,而是练功。出操练功由全队功夫最好的沈雄瑞负责,带领全队像专业演员练童子功那样每天先跑几圈热热身,之后压腿,把腿架在一个高台阶上,上身用力往腿上压,正腿压过了再侧腿,能压多低压多低;压完腿之后开始下腰,背靠墙壁双手往后扶着墙往下弯腰,能下多少下多少;下完腰之后再跑跳,这也是沈雄瑞时间,他带着大家先跑步侧手翻,然后跑步正手翻,难度越大,能做到的人越少,最后只有他一个能空手翻,赢得大家一片叫好。我们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干看就是不会。
每天出操我们倒不怕,是军人都要出操,最让我和小童头疼的就是练功了。练功那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开始练的。可我们都是快20岁的青年人,身体早已发育长成,腿压不低,腰下不去。但是因为是军人,我和小童其实都非常努力,用力压腿,使劲下腰。每天快到全体收工的时候,沈雄瑞就把我和小童叫到练功的毡子上仰天躺下,然后几个队友分别压住我的胳膊和一条腿,沈雄瑞抬起另一条腿扳直了往我胸前压,开始像试探一样慢慢地闪动着,突然出其不意地用力压到我们胸前,让脚尖压过头顶。顿时只觉得腿上的大筋触电一般的麻木,麻木过后便是剧痛。我实在忍不住大叫起来,身体早被队友压紧不得动弹。压完一只腿再如此这般压另一只腿。压完我再压小童,要不就先压小童再压我,反正我和小童两个新兵每天都要像过堂一样过过沈雄瑞这道关。
1974 年2月快到老兵退伍季了,这天高队长郑重其事地叫我去谈话,说队里决定我结束在宣传队的助勤工作,还回仓库连队。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雷打不动的一条铁律。我当然无条件地服从高队长的决定,就这样我在宣传队助勤半年又回到了仓库连装卸2排4班。
军人是有纪律,不负使命的。那时年轻的军人都懂得既然到了部队,就要学会一是服从,二是服从,三还是服从。1975年11师的文体活动非常活跃,除了部队的长项文艺演出之外,还举行排球、羽毛球比赛。为了积极准备参赛,团里从连队抽调一些有特长的战士在团部政治处前面的大礼堂集中训练。记得参加羽毛球训练的有1973年的云南兵李元,还有汽车连一个铁道兵2师的子弟(忘了叫什么名字了,新兵连我们还是同一个排的)。没下连队采访的时候,我常去看他们打羽毛球。小时候我也打过羽毛球,只是玩玩而已,球越打越高,只要球不落地能接过去就很开心。看李元他们打球,正拍、反拍、勾球、扣球、吊球、扑球、搓球、高球劈杀……直看得人眼花缭乱。我跃跃欲试上场跟他们比试两下,他们步伐轻盈地前吊后抽、 忽左忽右,羽毛球在他们拍下简直是随心所欲,要么打慢球跟我逗着玩,要么采用必杀技将球直击我身上无法还拍。累得我气喘吁吁,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羽毛球比赛是在滦平县城师部进行的,排球比赛却是在53团部外卫生队方向的河滩空地上举行。不记得53团排球队的成绩如何,只记得冠军却是51团排球队所得。他们的二传手是个四川籍战士,别看小个头,却非常灵活,托、垫、扑、传,不慌不忙,场上其他5名球员在他的指挥下打得很有章法。毕竟这种仅仅是有特长人员参与的集中训练比赛并不常有,军营文体生活更多的还是扑克、象棋。仓库连休息的时候,就围坐在大通铺的床上打扑克。我印象中四班长马头元扑克牌打得好,好在他把牌记得很清楚,几轮出牌之后,他就知道谁手里有大小鬼?谁手里哪门牌已绝?谁还有哪张大牌没出?都算的清清楚楚。对家如果没照他的意思出牌, 他准会大声地叫起来。象棋还是报道组组长王隆法排长下得好。休息的时候,将纸棋盘往地上铺开,两个人蹲在地上就开战。他出棋很快,似乎很随意,应对潇洒自如,但是招招都是狠手,让对方难以应对。谁跟他下棋都是来者不拒,但是在团部大院里我好像没见到谁下赢过他。
在团报道组的这段经历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我后来的事业发展和人生成长进步都有很大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战士来说,在团报道组相比在仓库连干装卸,工作要轻松(虽然脑力劳动也是很辛苦),行动也自由,而且也会有比仓库连战士更多的提干机会。但是,我还是想,在部队不管干多长时间,总还是要退伍。即使提干,也还是要转业。于是我想退伍。抽空回仓库连找到连首长谈了我想法,争取安排进1976年退伍兵计划之后,我才跟报道组组长王隆法谈了我的决定。王隆法不肯让我走,大概觉得我还是报道组可造之才,还想让我留在团报道组。他以为是连里强行安排我退伍。于是他说,我去跟你们仓库连说说,不让他们安排你退伍。我说,谢谢,是我自己要求的。王隆法再三挽留,见我去意已决,这才作罢。
退伍兵的专列是1976年4月4日下午从密云火车站出发,当天晚上到达北京丰台车站,第二天继续南行到达西安。我在西安下车,委托同我一起退伍的大毛将我的行李带回安康,我去了西安姐姐那儿玩几天。到西安之后才知道, 就在军列停留北京的第二天,北京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历史上称为“四五运 动”的大运动。

李康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1973年入伍,原铁道兵11师53团仓库连战士、文书,退伍后曾任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处长、铁道部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铁道部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公文写作在中央国家机关内部刊物、《紫光阁》杂志、国务院参事室《国是》、新华社《内部参考》、人民日报《内部参考》等发表;作家出版社出版长篇报告文学《风雪新天路》、铁道出版社出版报告文学集《中国高铁时代的新生活》、长篇报告文学《开拓者之歌》(合著)等。
编辑:岁月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