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 不能缺少的亮色
原创 |铁道兵张衍海
36
我探家期满,按时回到兵部大院一一
亲爱的北京,我又回来了!
接下来,与雪儿的交往,是一段相对频繁的通信时光。
写信,成为我们唯一的交谈方式。
信发出去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那些日子,除了工作就是写信。守着一份宁静和透明,不再关心外面怎么喧嚣、怎么变化。因为有了几分对别人的和别人所给予的牵挂,生活十分充实,精神十分饱满,心情好得不得了。
做梦都梦到全世界人民都解放了,太美好了!
一一北京好,家乡好,全世界都好……
从两年前算起,到北京以后的日子里,我沉浸在一片崭新的氛围中。每天享受着工作的新鲜感和希望的万花筒般的诱惑,这情景无论多么现实,我却仍然恍若梦中。
一一因为一切都来得太快了,快得让我来不及思索,来不及应对,甚至来不及调整自己……
在我的潜意识里,我仿佛觉得自己还是一棵植根于荒野的小树,忽而被移植到一处完全陌生的园林里,与周围的名花贵木总是有些格格不入。虽然我有我的姿采,我有我的形态和特色,我的出现已经让很多人感到惊奇,但我仍然感觉栽我的这个形制优美的小花盆并非是我的长久立足之地。
军训处的和教材组的人都对我很好,从处长、副处长到各位参谋,他们像关爱自己的晚辈和小弟弟一样关心着我,爱护着我。
那时候,首都经常有一些大型文体活动,赠票发到各个单位。由于票少人多,军训处就把我列为“重点照顾对象”,别人不去也得让我去。
没过多久,像人民大会堂、首都体育馆、工人体育场,还有各大公园,我都去过了,有的地方还去过多次。
有时候,中央和国家领导人也会出席大型活动,人山人海地远远望见,感到莫名的荣耀。
我在做好美编工作之余,还主动担当一些书稿的校对、勘误,以及去出版社、印刷厂送稿取样工作。
军训处上上下下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几次报请司令部机关给我奖励。
曾经有人给我“交底”,按这个趋势走下去,两三年之内,我有可能就要在军训处提干了;因为绘图工作是军训处不可或缺的,在其他方面再学习提高一下,当个参谋指日可待。
然而,我的“目标”不是在司令部的哪个处当参谋。我是想正正经经地画点画,搞搞创作。而我想要去(同时人家也欢迎我去)的地方,那时恐怕只有美术创作组了。
美术创作组是文艺创作组的一个分支一一
兵部文艺创作组已经很庞大,成员有:朱振声、王孟强、吕希杉、冯复加、叶晓山、李武兵、朱传雄、冉淮舟、严歌苓、李克威。以上这十位都是作家、诗人、散文家。再加上两位搞美术创作的,一位是黄嘉善,一个是路巨鼎。铁道兵政治部文艺创作组总共有十二个人。黄嘉善负责组织了“业余美术创作组”,有“业余”两字,就说明是不在编的;人员也不固定,有时多,有时少;人数最多时,有三十多人;人数少时,有不超过十个人。这些人除了有少数搞油画、国画创作的,多数人是以集体创作的形式搞版画创作。
当一名创作员,全身心地投入到我所爱的艺术中去,是我在那个时候的不二选择和奋斗目标。
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我委婉地向领导提出:我要加快工作进度,尽早把所有插图和封面设计都做完,然后专心去搞创作……言下之意,按现在的“流行语”是一一我要“跳槽”了!
我的敬爱的处长、副处长和丁参谋、徐参谋,还有教材编绘组的所有人,都用不舍和不解的眼神看着我,想尽可能地挽留我。
这个话题有些矫情。
不过事情确实是这样,不知道心里是啥滋味。

消息很突然。
我试了好多次,才终于张口说出来。大家都对我那么好,一起工作快两年了,我会的都是他们教我的。突然说要走,我怕是背上了“背叛”的嫌疑……
叛徒?
我不会当叛徒!
我忠于的,始终是我所爱的事业一一
世界欠我一个初恋,我连去寻找她的机会都没有了么?
一一我心里是这样想,但是却没有勇气说出来……
话不多说。
说多了,都是泪。
换了谁,谁都会心有同感。因为你不舍得把自己蚌壳里忍半生疼痛磨出来的珍珠挂在别人脖子上炫耀。
不用解释,也无须解释。大家都了解我,我也理解他们。
叶子想要离去,不是大树的枝条不想挽留;而是季节换了,秋风中有叶子的追求。追求的结果,可能会很残酷。它将失去水份的滋养,逐渐干枯,直至变成一片薄薄的、又很容易碰碎的雕塑……
但是,它依然坚持着要随风而去,以赴死的决心去完成它最后的心愿!
我终于明白一一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叶子,都长成了心的形状。
帮助过我的人,我将永远记住你们!
真情常在,友情永驻一一
一切,尽在心里……
我记得领导还专门找我谈过话一一
一方面,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再一方面,对我今后的发展表示了乐观;最后,又一次表达挽留之意……
但我的决心已定,领导只好高抬贵手,放我一马。
两年了,我的“实力”(档案关系)还没有迁来,领导也有领导的“软肋”……
领导无语了。
不过,领导提醒我一一我所面对的工作量是巨大的,46种教材的插图和封面设计,原计划是干三年,最快也得两年半才能完成,完不成就无法向首长交代。
我说我保证在年底(也就是1973年的年底)前,圆满完成任务,不完成任务绝不走人。
领导这才放了心。
从那个时候起,加班加点就成了我的家常便饭。
说起来也怪,人要是直直地奔着一个目标走,心里就会很敞亮,干活一点都不觉得累。
后来,我学会了“偷懒”,发明了一种“借用法”一一就是在插图背景不变的情况下,借用同一背景,只换人物;比如我在画《排除美帝磁性弹的方法》和《线路工》、《爆破工》等教材的插图时,只须在一个组图中画好一幅背景,人物动作和手势则分别单画,省略背景,然后剪下;用红笔划出十字标记,标好人物在背景中的位置,加写说明,方便拍照。制版工人一看就能明白,从而大大加快了我的工作进度。
内行的人都知道:在单色(黑)图版中,红颜色是不影响制版的。
就在我快马加鞭加班加点努力工作的时候,有人来添乱了!
那个以擅写理论文章而被当成“如椽之笔”的刘红专,两年前的那次学习班我和他有过接触,仅仅是认识,彼此都知道对方叫什么而已。他的名字很好记,又红又专,带有时代标记。人怎么样,没有深交。
我还知道他被留在了师宣传科写作组……
刘红专是带着几篇“大稿子”和“一炮打响”的决心加信心来到北京的。他也想步廖观如的后尘,以“革命工作一盘棋”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剥削我这个“无价劳动力”,让他的“大作”金蝉出壳。
他来找我了一一
天底下竟然还有这样的人,一点也不把自己当外人。
一一那当什么人?
一边唱着高调,一边下达任务……他把自己摆到领导的位置上,还觉得理所应当。
一一什么领导呀?他只不过比我早当半年兵,都穿一样的两个兜的军装。装什么“大尾巴狼”?(这话,我可不敢说出来,怕影响团结。)
我一边挨着训,还一边给他干……
冤不冤哪?
一一比窦娥还冤!
我不怕别的,就怕他真是奉了老单位领导之命,到北京来找我。若是我不配合,他回去再告个小状,我得费多大劲才能挽回影响呀!
不能做到忍辱负重,那就只能忍气吞声了……
不过,我还是保留底线的。我不能让他像廖观如那样喝了酒不认账,只顾往床上一躺,什么活都一推六二五,自己的地不种,只管收庄稼……我得先把他的后路堵住。于是,我装出一副特别诚恳又爱莫能助的样子,对他说:
“你看,我就是一画画的,写东西是外行,帮不了你多大忙。要是你实在需要我帮忙,你写好后,我只能帮你抄一下……”
未了,我又强调一句:“我,是真不能写……”

刘红专略有失望地叹了口气,随即,那一点点失望的表情马上被强大无比的自信的神色所取代,他说:
“你若真不能写,也不难为你了。那就抄写一下,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嗷!”
末了,他也强调了一句:“这可是往顶尖大报送的稿子,一旦发表,影响可就大喽!”
刘红专双手插在两个裤兜里,得意地吹着口哨,开始在房间地板上有节奏地走起了正步。一直走到楼下有人找上门来,善意地提醒他“动作轻一点”,他才觉出了自己的荒唐,嘴里连声说:“失态了,失态了……”
寂静突然就降临了!
在他眼前,宇宙空旷无垠,星星飞旋着四散而去……
我看他得意忘形的样子,有些莫名其妙。费尽心思地琢磨着一一这人怎么像吃错药了一样?至于吗,就那点还没等着由手写字变成铅字的文章……
琢磨来琢磨去,心里翻腾着一句不太中听的话一一
“这东西,不长时间就成废品!”
我终于还是忍住了,没把那句不中听的话说出来。
一一刘红专同志是接受不了的。
他在宇宙中,还未回来……
不知道是正中下怀,还是歪打正着,反正一一我“不能写”的印象,就在星星们飞散而去之时,实打实地让他记住了。
能别人所不能一一他的自豪感和成就感,在宇宙中,油然而生!
也就在刚回到北京的那几日,“西哈努克”打电话让我到美术组来一趟,说有事商量。听电话里的口音,我感觉神神秘秘的……
正巧,我也好长时间没去,想那帮哥们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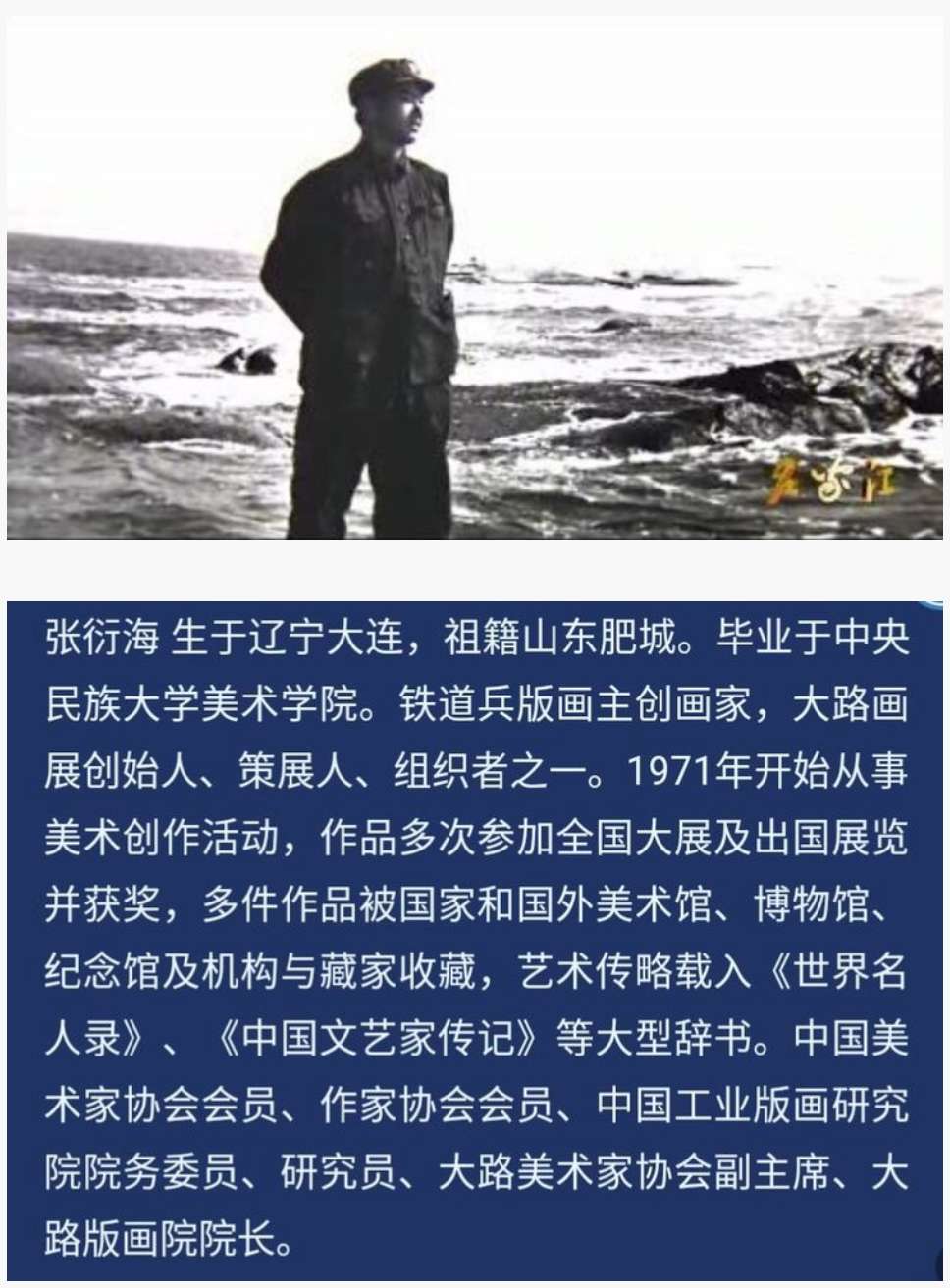
未 完 待 续
编辑:向日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