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1969~1970 那个跨年的冬天
原创 |铁道兵张衍海
我叫路远。这是我的化名,也曾经是我的笔名,很多年前用过。其实名字无所谓,因为我要讲的故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一一
我是在珍宝岛战役打响的那一年秋后当的兵。那一年,也就是1969年,国家征了两次兵,早春一次,晚秋一次,这在共和国的征兵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本来,我在春天那次征兵结束时,就差一点走了。只是因为公社坚决不同意,要留下我去农村中学当民办教师,才没能走成。从走了的同学来信中得知,新兵上车后,接兵的南方部队干部还在满车厢找我。假如我跟新兵一起上了车,手续都可以后办,很有可能就成了比现在早半年多的兵了。那时候,部队有一个说法:早当一天兵,也算是老兵。
秋后征兵,我决心已定,谁也拦不住我。一路斩关夺隘,最终如愿以偿。新兵集合以后,发放服装用品,编成班排连,召开出发誓师大会。指导员钟守良让我代表新兵一连全体新兵发言,其实就是表决心什么的。会后,各连新兵被允许回家住一晚,和家人告别。
最后要离开家的时候,我最小的妹妹刚刚出生,这是我母亲生下的第十个孩子。我在家排行老二,哥哥先我当兵走了,他是1966年入伍的兵。我走那年,哥哥刚被提拔为空军某部雷达连的排长。
说不清为什么,走的那天,我谁也没让送。穿上刚发的草绿色军装,就差领章帽徽没有,那是要到部队才能发的。天刚蒙蒙亮,吃完了奶奶给煮的一碗荷包蛋面,我就上路了。那时,我只顾着急忙慌地走,哪顾得儿女情长?在我身后,有父母潮湿的眼睛,一直在朝我望。我这辈子,始终都没走出父母的目光……
我家住的百尺村离老县城大约有两三公里,火车站就在老县城边上。我背着军被打成的被包,肩上还斜挎着一只崭新的挎包,沿着那条被独轮车和老家人叫做“地排子”的平板车轧出条条轮痕的土路,一个人岀发了。越过村子西边的果树林,爬上一个巨大的缓坡,这个土坡是开挖水库时挖出的黄土堆积的。土路两旁,长满了带尖刺的酸枣丛。不远处,有一片古墓,传说是明朝初年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徙而来的老祖宗和他后来的子子孙孙们的安息之地……再往前走,有一股裹着怪味的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一一康王河近在眼前。
俗话说,“冤家路窄“。这里没有冤家,这里路也不窄,可是偏偏这个时候,让我遇见了最害怕见到的一个人。他是谁?他就是西胡同里的秦铭大爷,一个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

话从三年前说起一一
因为我家里人口多,没有壮劳力,所以在学校放寒假时我就到生产队的芽子池去干活。芽子池是我们这儿当地的叫法,其实就是培育地瓜生芽的温床。这温床是用土坯砌的,长方形,每个约有半米高、两米宽、十米长。下有烤炉和烟道,以便产生和分散热量;上有草苫子,夜里覆盖,白天打开;中间有沙子埋的地瓜种和冒出的新芽;需要每天浇水生火,保持湿度和温度;待到载秧时节,三四月间,芽子池的使命便告结束。
和我一起在芽子池看夜烧炉子的还有延喜四哥,我们俩挤在一个用玉米秸搭成的窝棚里。窝棚不大,俩人钻进去确实有点挤,别说转身了,就像钻猫耳洞一样。差别就是,钻猫耳洞没有声音,钻窝棚却哗啦哗啦响,外边老远就能听见。
延喜四哥刚结婚,他就跟我商量,让我前半夜多留神,后半夜他从家里回来,有时早有时晚。我说没事儿,你就多陪陪嫂子吧。因为头一年就是我们俩搭伙,合作得挺好的。虽然头一年他还没结婚,但是对象是跟我们邻村的,也没断了夜里出去约会。
事情错就错在太大意了。有一天,发现支撑草苫子的木棒少了四根,肯定是被偷了,谁偷的,没抓住。木棒是秦铭大爷借给生产队的,他说那是四根檩条。既然说是檩条,那就得有碗口粗了,木棒还没有胳膊粗。东西不在,也无法验证了,只有赔吧。生产队让我和延喜四哥每人赔两根,相当于各打二十大板。我回想了一下,那天晚上填完炉子,我就在马灯下看书,可能是太入神了,也可能是偷盗者发现窝棚没有响声,才敢下手的。总之,我有责任,甚至责任更大些,只能认罚。我愧疚地求告秦铭大爷,千万别将此事告诉我家里人,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迟早要还上这笔账。
那时候,我正在上中学,住校,每个星期回家一趟,取干粮,基本上是地瓜面煎饼。从打出了这个事以后,我就不敢走西胡同那条老路了,绕着走,就怕遇见秦铭大爷。我并不是想赖账,我心里记着哪一一等我有能力挣了钱,我一定还他,加倍!
说实话,我们家在村里口碑一直不错。日本鬼子时期,我爷爷因为给八路军办事暴露了,带着他的两个儿子,也就是我父亲和我伯父,一路颠簸到了大连,在那里慢慢地就定居下来,也给后来闯关东的乡亲一个落脚地。我伯父参加抗联,和日本鬼子打了几仗就没信儿了。我爷爷活到我出生刚满周岁,据说是因为解放了,又有了俩孙子,高兴得天天喝小酒,终于有一天睡过去没能醒过来……我父亲是抗战后期在兵工厂入的党,解放后转到石油战线工作,曾任石油八厂工会主席。后来又奉石油部的命令带领一批骨干支援青海油田建设,把我们全家舍在东北,他去了大西北。在柴达木盆地,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加上战争年代在兵工厂造火药患上的矽肺病折磨,他终于病倒,被单位派人送回内地疗养。他的病总也不见好转,单位就让他长期病休,啥时好了再说。到了1962年,父亲回了一趟山东老家,见到了我奶奶和跟着我奶奶的我哥,祖孙三人抱头大哭。哭罢,父亲打定主意:回老家来!于是,就有了半年后的举家南迁。
那个时候,也许是父亲应接不暇,抑或是他力不能支,或者是另外还有什么疏漏,回老家落户的时候,全家人的城市户口没了一一为国家做过贡献和牺牲的这个家庭竟然成了“黑户“!在我父亲为全家落户的问题四处碰壁焦头烂额的时候,老家毕竟是老家,最终敞开胸襟接纳了我们……从此,我们全家变成了农业户口。青海石油管理局还照常给我父亲寄发病假工资,每隔一年还派人专程前来看望。送工资汇款单的邮递员都纳闷:这位国家干部竟然还是农业户口,真是天下少有。父亲听见,只是一笑。工资到手还不等热乎过来,借钱的就登门了,父亲总是来者不拒,人家借,他就给……
就在“檩条事件”发生后不久,秦铭大爷找到我家里来了。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来讨债的,心里想,大爷呀你真不守约定,我说了我肯定赔偿你,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秦铭大爷和我爸爸在宅院里嘀嘀咕咕,欲言又止,我听不见他们说的是什么,却又不敢靠近。过了一两分钟,父亲拉着秦铭大爷的手,往堂屋里让,又招呼着我妈沏茶水。秦铭大爷连连摆手,说不用了。这时候我爸爸就拿出两张大团结,递给秦铭大爷。等秦铭大爷走了,妈说了句:“又是来借钱的”。钱借出去了,还没还,父亲再也不提此事。
我默不作声地干我自己的事。既然秦铭大爷不说,那我也不说,把这件事烂在心里。该我还的,我早晚要还。大爷,你放心吧!这半年里,我在农中当民办教师,只挣工分,不拿钱。所以,那钱还得欠着……
康王河在百尺村边由东往西,再拐一个弯儿,缓缓向南流去。拐弯处,有一座铁路桥横跨东西。土路贴着桥西头,沿着铁路路基通向火车站。这条只有几十公里长的铁路线,原先是由铁道兵修的运煤专用线,东起津浦线上的泰山站,西至桃城矿区。离我家不远的桃城站,是沿线最大的一个站,每天除了拉煤的火车经过,还有早晚对开的旅客列车。

我真没想到,秦铭大爷会在这个时候出现,而且是等候在我离开家乡的必由之路上。虽然已经入冬了,天还不算太冷。秦铭大爷裹着一身破棉衣,肩上和袖口都露着棉花套子,腰间扎着一根草绳子,头上棉帽的两个护耳舌一煽一煽的,脚上的破棉鞋露出脚趾头。在他身旁,立着一个用紫穗槐枝条编的旧粪筐,还有一个粪铲子,铲子把足有两米长一一这铲子是拾粪和甩土石块两用的,一般是放羊人的装备。
他的羊呢?河岸上和铁路旁的土沟里,星星点点的白色物状,便是他的羊了。这是他的生计所在,他的晚年所依,可怜的老人啊!
他像一截老树桩似的伫立在路边,纹丝不动。只有白色的胡须在微风吹拂中飘动几下,脸上像挂了霜一样。
走近了,我先跟他打招呼,心里七上八下的。
“大爷,您怎么在这儿呀?”
秦铭大爷的嘴巴动弹了几下,很不利索地说道:“我……我,我……等你啊,二小!“
这时候,我已经知道自己逃不过了。索性,破釜沉舟吧!我不自觉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口袋,掏出了所有的钱,都是零的,加起来还不到十块,一把塞给他。
“大爷,您先收着,剩下的,我给您寄……“
老人像触电一样,不停地推让着,连连说:“二小,二小……你听我说,我不是,不是那意思……我就是想来,送送你……”
我心头一热。
“不管是啥了,这钱,您一定收下!”
“我听说你要走了,本来昨晚上想去找你啦啦呱,又怕耽误你和你爸你妈说话,我,我就没去。这不,今儿一早,我就搁这等你了……“
我顿时语塞,不知说啥是好。
对面的老人,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铁道兵团退伍老兵,苍老的眼眶里泪花闪闪,像干枯的老井又冒出了泉水。他那双老树皮一样粗糙的手,颤颤巍巍地,把钱接住,又从里边抽出两张一块的,不容分说地递给我:“二小,你……你接着。你大爷我知道,当兵的到处走,走到哪儿,渴了,买杯热茶水喝;走得远了,别忘了给家写信……“
这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一扭头,眼泪啪啪地砸在地上,溅起尘土。
“二小,快走吧,不耽误你时间了。以后是国家的人了,时间金贵。走吧,走吧!”
我走了,这是秦铭大爷说给我听的最后的话,至今不忘。故乡对我有恩,故乡人对我有恩,我总觉得欠下了什么,今生报答不完……
战士出发的行装里塞不下太多的东西,能放下的尽可能放下,放下之后,终于可以轻松地上路了。我走过一段距离之后,回眸东望,这算是告别家乡的一个注目礼吧。
晨雾在康王河谷迟迟不肯收尽,朝晖又迫不及待地想撒下一张无处不在的巨网。依山傍河的百尺村在晨雾朝晖的夹缝中炊烟枭枭,一些鸟儿在铅灰色的天空中盘旋着,盘旋着,就要开始飞翔了。然而,谁也没有注意到,那些鸟儿的翅膀有多沉重。刚才还有些见亮的天空,这会儿却神不知鬼不觉地阴了起来,要变天了……
走进站台,耳畔传来火车汽笛的鸣叫声。新兵们正在背着行装,整理队伍,按班排连的顺序登车。这个时候的我,已经被临时任命为新兵一连一排一班的班长,是第一个上车的。再过几分钟,这列拉载着十几节闷罐车的火车专列将要开动。我知道,我已经把自己的十八岁留在了这条铁路边上,留在了故乡的原野里。

张衍海版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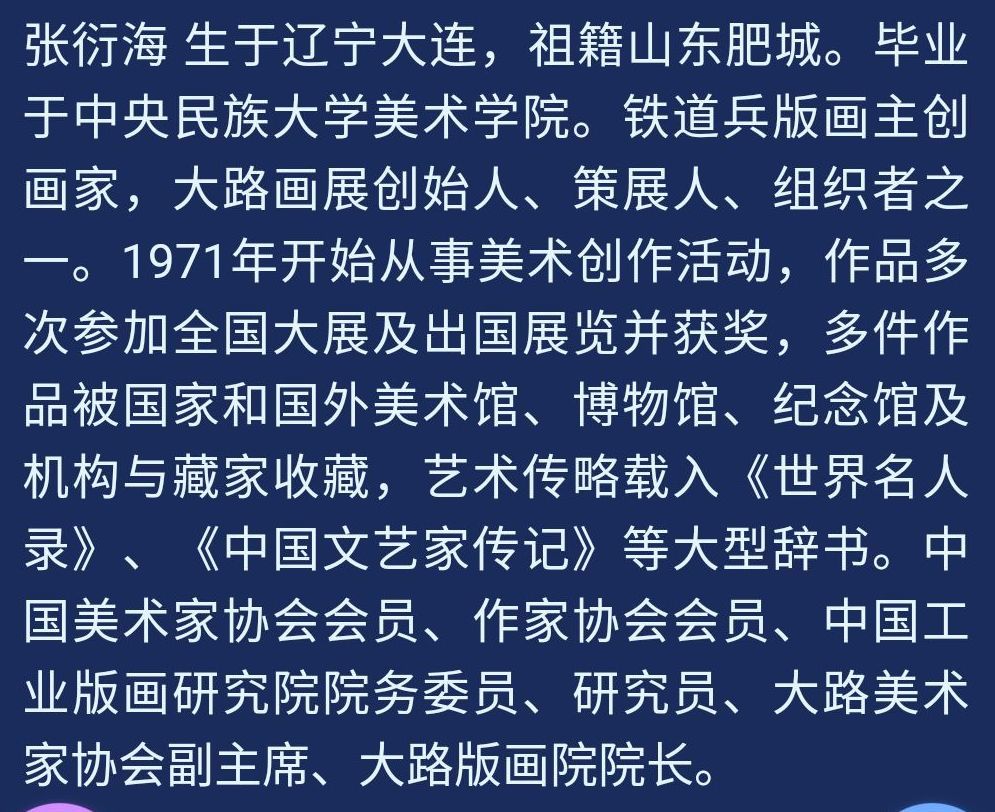
未 完 待 续
编辑:向日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