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1969~1970 那个跨年的冬天
原创 |铁道兵张衍海
2
列车开动的时候,天空开始飘雪。车轮越往北疾驰,雪就下得越大,天地间都是白茫茫一片了。闷罐车里没有坐席,只铺了一层麦秸,连席子也没有。那时候,也不能讲什么条件了,根本就没条件。白天,新兵们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己的背包上,有时拿出和巴掌差不多大的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各自读着;有时搞点文娱活动,各班拉歌。拉了几首歌以后,未分出胜负。三班那个名叫辛贵全的新兵班长讨厌死了,公鸭嗓子一个劲地叫唤,隔差车皮半里外都能听见,一看就是个好出风头的家伙。指导员钟守良大概也不太喜欢他咋咋呼呼,光是声音大不说,还跑调,八头牛都拽不回来,真让人开眼了!钟指导员在老部队是团业余宣传队出来的,可以说不缺文艺细胞,他要教新兵们唱一首新歌《铁道兵志在四方》。
背上了行装扛起枪,
雄壮的队伍浩浩荡荡。
同志啊,你要问我到哪里去?
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美妙的歌词和动听的曲调顿时深深感染了大家。据说,这还是周总理爱唱的一首歌。这时候,每个新兵,包括我,才对我们即将加入的铁道兵部队有了感性上的认知。一切都是新鲜的!自我感觉良好的辛贵全在领略了钟指导员字正腔圆的歌声之后,终于消停了。他大概是在想,真的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到了晚上九点,随着熄灯号吹响,全体新兵都把背包带解开,一个挨一个地将被褥铺在麦秸上面,人挤人钻进被窝里。列车“咣当咣当”的声音,成了整个军列上的催眠曲……
夜已深。很多人都睡着了,有人还打起了呼噜。渐渐地,此起彼伏的呼噜声由小合唱变成大合唱。三班的辛贵全就是领唱。这货,像牤牛犊子啃了小刺猬一样,那动静,让耳膜受损!
在辛贵全带头制造的噪音包围下,我醒着,睡不着,碾转反侧,却又无力组织反攻。

旁边是钟指导员,他好像也没睡着。黑暗中,他用胳膊肘子碰了碰我。我动一下身子,算是给他的回应。一个轻轻的声音在我耳边问:
“怎么啦,睡不着?”
“嗯。”
“想家啦?”
“不是。”
“那就说说话。”
“指导员,咱们这是要去哪儿?”
钟指导员没有马上回答我。我知道,我可能是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军事秘密。
“路远,你真想知道?”
“嗯。”
“好吧,我告诉你,只能有限地传达到班长一级,暂时不要对外扩散……”“我保证……”
“大兴安岭一一我们铁J师钢一团驻扎的地方……”
大兴安岭?我不再问什么了,知道那是我们国家版图的最北边,离边境交火的地方肯定不远了。沉默良久。脑子里的思绪在飞快地旋转,想一下子找出它的定位,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信息……
漫天飞舞的雪片,仿佛是北方遥远的山岭和灰蒙蒙的天际送出的请柬,随风飘啊,飘啊,飘到我的面前。我该接受这些请柬吗?这些请柬是跋涉千里专程飘来送给我的吗?不光是我,还有这趟列车上所有穿上军装的人,人人都面临如此的叩问。如果是在和平的年代里,雪花可以被看作是冬的繁花,冬的絮语。而现在或将来的某一天,假如一场大的战争突然爆发,那么雪花对于军人又意味着什么?也可以是警报,也可以是战书,还可能是荒野新坟前旋转的花瓣……
悲壮,这就是临战当兵的热血男儿挥之不尽的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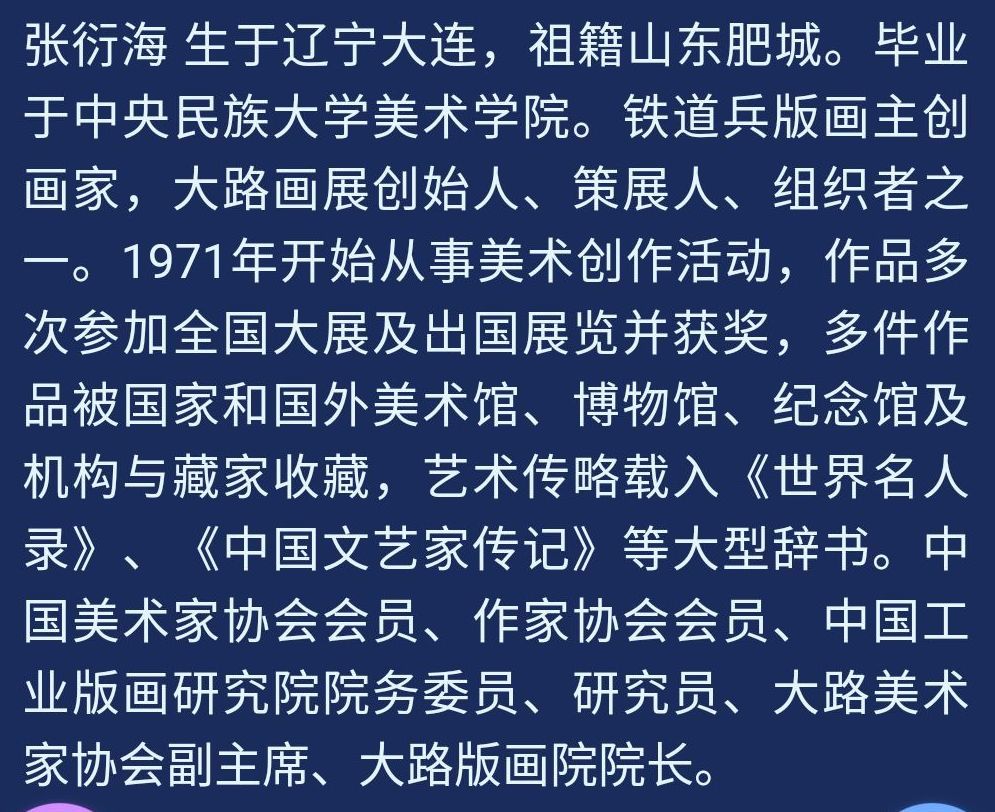
未 完 待 续
编辑:向日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