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我出生于一九五二年五月,祖籍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于一九七一年六月加入中国共青团组织,一九七三年一月参军,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一九八零年一月毕业于长沙铁道兵学院。在部队期间,曾先后任副班长、班长、排长、学员、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一九八四年,我随铁道兵部队集体转业到铁道部第十六工程局第四工程处,先后担任过施工队书记、处纪委办主任干事、人事科主任干事、安全科副科长、企业管理部部长。我于二零零三年一月份退居二线,并于二零一二年五月份办理退休手续,其间,自二零零三年三月份开始,我先后考取认证行业的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实习审核员证书》、《审核员证书》、《高级审核员证书》资格,从此,我在认证机构作审核工作时间长达十年。二零一三年五月份,由于认证行业年龄限制到期,我不再从事审核工作。同年八月份,经本人申请并经考试合格,我被聘为兴原认证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合格供应商评审员”。从此,我在该机构作评审工作五年直到二零一八年。之后,我正式退休并扮演新的角色——当全职姥爷负责照看外孙。
我所撰写的《放牛娃出山之路》一书共分四大部分,主要反映四个阶段的人生经历:第一回,山村里长大;第二回,光荣从军十二载、大山深处展风采;第三回,兵改工路上,饱偿着艰辛;第四回,老有所为,夕阳灿烂。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内容不免有不当之处,恳请读者看后,多提宝贵意见,谨表示万分感谢。
鸣谢:
在本书编撰过程,我的亲家赵仕闯先生、赵秀兰女士以及我曾经的同事高级工程师孙红绵女士都花了大量的时间给予文字上的修改完善;我过去的同事牛玉战先生在国外尼日利亚还抽出时间帮我改稿。胡国群先生、刘德辉老师、范继红老师等给予在文字上的指正;我的闺女张小花、女婿赵晨光提出一些文字修饰建议并给予在编撰过程的支持和出版环节的业务联系。对此,我表示衷心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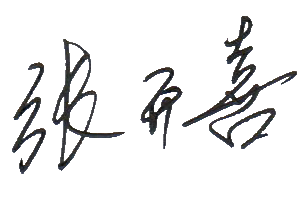
放牛娃出山之路(1)
作者:张开喜
第一回
山村里长大(1)
出生在土改时期
一九五二年,我国继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又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这就是全国的农村土地改革。后来,我听父亲说,就在这一年,我家也分得了房子和田地。该房子是原地主邹昌典家的一部分,西侧三间归我家,其中有两间正房、一间厢房。东侧房子被分给了邻居王家。整座房子坐落在龙王寨脚下的刘家院子。当时,刘家院子包括有刘、张、王、邹等姓氏家族。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五日,我就出生在这座老房子里。由于共产党、毛主席给我家分得了房子和田地,我们张家人脸上才开始出现了喜悦。我因为在这时期出生,所以,我的爸爸给我取名张开喜,乳名喜娃子。在我们老家,对孩子的称呼,都习惯在其名字后面加上“娃子”,一直到长大成人之后,家人或邻居才开始叫其大名。看来,爸爸给我起名张开喜,这也是有时代意义的。
后来,我参军入伍。服役期间,我先后几次回家探亲。每次探亲,我都听到老家一些人说我家住的哪座房子风水好,说东侧出了个王祖国(我的二表哥),西侧出了个张开喜,都在部队当军官。二表哥是我家隔壁王家表叔的二儿子(后来因为二表哥娶之妻同我婶子同姐妹,我从此改口叫他姨父)。当年,二表哥当兵时,我年纪尚小,记不太清,但听说他打过仗,先后参加过平息西藏叛乱、中印反击战等战役,在部队曾多次立功授奖,先后当过副班长、班长、排长、连队副指导员、指导员、独立营副教导员、教导员,师直政科长(兼直属党委书记)。从部队转业后,他开始在汉中市汉江监狱当监狱长(兼党委书记),在担任监狱长期间,曾先后立二等功。后来在陕西省监狱管理局当副局长等职,2000年光荣退休了。至于乡亲们提到我,我倒觉得自己算不上什么官。当然,乡亲们习惯把在部队提升为干部的军人叫军官。我曾在部队当过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等职。1984年1月1日,我随所在的铁道兵部队百万大裁军集体转业,我在企业工作的职业生涯后期当了个正科级干部。虽然我们共产党人不信什么“风水”,但我和二表哥童年都是“放牛娃”,我俩都没有上过几年学,靠的是部队领导的培养和教育以及同志们的帮助,加之我们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才有了今天。
农村吃食堂
我六岁开始记事。我记得1958年全国大跃进、农村吃食堂时期,每天早晨,比我大的表哥、表姐们都背着书包赶到食堂吃早饭。当时,生产队的公房叫“农场”,食堂就设立在“农场”里。冬天,食堂里的早饭都是蒸红薯(老家把红薯叫红苕)。一群“学娃子”(老家把学生叫学娃子),每个人手上拿着两个蒸红苕,一路欢声笑语的上学去了。我常常想起在集体大食堂过春节的情景。大年三十吃年夜饭,集体会餐,开饭时,基本上是一家人够一席的就坐成一席,一家人不够一席的别的家人补满一席。年夜酒席有酒有肉,可是我年纪小不懂事,正式吃年夜饭时,不好好吃,吃完饭后,轮到别人吃饭时我又眼馋,有时候还在地下捡骨头啃,妈妈看到后也顾不上是在过年,当场就给我了一巴掌并拉着我回家。回家路上,我一路哭泣。我记得应该是在1960年,农村停止了吃食堂。有一天,生产队把锅、碗、瓢、勺以及一些农具集中在大晒场上,按其价值分成若干份,然后由各家农户抽签领取。从此,农村集体的大食堂制结束了,又恢复了往日的小家庭生活和大集体劳动模式。
小学生活
一九五九年七月,我时年七岁并开始上学。我的学校在吴家山祠堂。这家祠堂过去是吴氏家族祭祖的地方,解放后才是小学,取名为新塘小学,该学校距我家大约有二公里路。“新塘”源于我们大队的名字。解放初期,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大队新修了很多的堰塘,用以蓄水旱季灌溉稻田之用,因此叫“新塘大队”,学校因此也就叫新塘小学。整个学校只有两个教室,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在一个教室,两个年级从左至右排列,各占两列。学校只有两位老师,我记得一位是周老师,他教一、二年级,还有一位是杨老师,他教三、四年级。老师给前一个年级讲完课、布置复习后,再给下一个年级讲课。不同年级之间的学习干扰肯定是有的,但没有办法,学校也就这个条件。在学校里坐的板凳,都是我们学生自己从家里带去的,开学时扛去,放假时再扛回家。我们学习用的课桌是用木板和砖墩子架起来的。由于那时学校经济非常困难,各种教学设施都十分简陋。冬天,学校没有取暖设施。有条件的同学提着个火笼子上学以备上课时取暖用。这种火笼子是篾匠用竹子篾编制而成,好像灯笼一样,里面放着一个陶制小火盆儿。早晨,妈妈在火盆里放上一点火种,再放上一些木炭,然后用热灰盖起来,这样能保持炭火在一个白天内不会熄灭,能散发一定的热量,孩子们就靠这个小火笼子取暖。下课时,在火笼子烧爆米花,吃起来特别的香。有时候,我从家里偷着抓一把包谷(玉米)放在书包里,等下课时,我就烧爆米花吃,馋得旁边同学直流口水。
我家兄弟多,我是老四。在那物资十分匮乏的年代,人们生活十分的贫困。因此,我们这些小孩子穿不起什么好的衣物,我的衣服、鞋子都是我哥哥穿过的,我把旧衣服拿来穿在身上,又大又长,从后面看,好像一个老太婆,走起路来扑塌、扑塌的,特别是下雨天,走在黄泥路上,脚上的大鞋子采在黄泥坑里,拔不起来。每到这个时候,我总免不了哭一场。后来爸爸给我想了一个办法,把草鞋套在布鞋上,这样走稀泥路既防滑,又牢固。当然,每到过年的时候,妈妈还是会给我们每个人缝一身新衣服。新布是爸爸将妈妈平时用棉花纺的线,织成“土布”,然后再送染房染上颜色,一般为蓝色,也有染黑色的。妈妈用土布给我们缝一身新衣服,新鞋子。过新年,我们穿在身上也觉得挺美的。
一九六三年,我上完初小(在我们当地,小学分初小、高小,一、二、三、四年级为初小,五六年级为高小),升到高小。这所高小名为“双乳小学”,位于双乳铺街道东侧,隶属于双乳公社,距我们家大约五公里。“双乳”,源名于月河两岸对称有两座小山包,好像一对乳房,老人们都叫它奶子山。两山之间是月河,河流宽约50米。平时河水只有一米多深,水面宽度也不过20多米。夏天下爆雨时,月河流域沿途两边山洪汇集,涨水可达10多米深。每到涨水时,月河给我们这些学生们上学带来了极大的交通不便。平日里,冬天,人们要到河对岸去走的是独木桥,到了夏天,人们可以趟水过河。在洪水大的时候,人们能乘坐渡船。但是,在洪水特别大时,河流很急,渡船停运,我们只能被困在学校。因为我们身上没有钱,肚子饿了也没有东西吃。有时候,饿急了,我就跑到亲戚家去蹭饭吃。冬天过独木桥很危险。记得有一天,老师带我们班同学去双乳小学开会。我走到独木桥十多米处,突然觉得头晕眼花,水向下流,桥向上跑,一时站立不稳,扑通一声,我掉进河水中。当时是蓝志新老师跳进河里把我救了起来,她把她的棉衣脱下来给我穿上,让我回家了。蓝老师做为一名女老师,她舍己救人的英雄行为,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心存感激。后来,我从部队回家探亲,曾多次打听她,但是,最终我也没有找到蓝老师。
上五年级时,我有两个好伙伴,一位名叫顶娃子(大名王宗顶),还有一位叫老四(大名叫邹荣成)。老四的钢笔字写得特别好,我很仰慕他。每天早上吃完早饭,我们就一块上学去。每天下午四点放学回家,一进门,妈妈就唠叨说:“喜娃子,饭菜在锅里,趁着肚子饿了先吃一碗红苕,红苕上面的米饭,留着你明天早晨上学时热着吃”。说实话,因为平时总吃红苕,都吃厌烦了,真想吃那一碗白米饭,但是,为了明天早餐,我只好吃两大碗红苕,好在肚子饿了,吃红苕也很香。这一年,我也就十二岁。上学的每天早上,我自己起床,自己点着火热昨天留的那碗米饭,吃完就上学去了。我们这些距学校远的学生,是吃了早饭上学,学校附近的同学,他们都是上午十点放了“早饭学”回家吃早饭再来上学。我们路程远的同学都是天不亮就吃早饭上学,却要坚持到下午四点放学回家才能吃上中午饭,每天放学时都非常饥饿,因为,在学校期间,没有什么东西可吃。想想现在的孩子,你说有多幸福,吃的、玩的,零食,玩具应有尽有。可我们的童年,能吃什么、玩什么?上学时,悄悄带一个生红苕或一个生萝卜,还怕家长知道。玩的就更别说了,钻草堆、捉迷藏、滚铁环、打陀螺(自制),就算是我们最好的游戏了。就连学校的体育课,也只是跑跑步、踢踢毽子、跳跳绳。在我参军之后,第一次回去探亲,我先后回到我的两所母校,看到学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塘小学不再是过去的祠堂,而是换了位置,新盖的校舍,还统一配置了新的课桌和板凳。双乳小学还是原来的位置,也盖了新房,增加了不少老师,学校焕然一新,虽然不能跟城市相比,但至少也比我们那个时候的条件好多了。(未完待续)
图片来至网络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