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女兵的第一个军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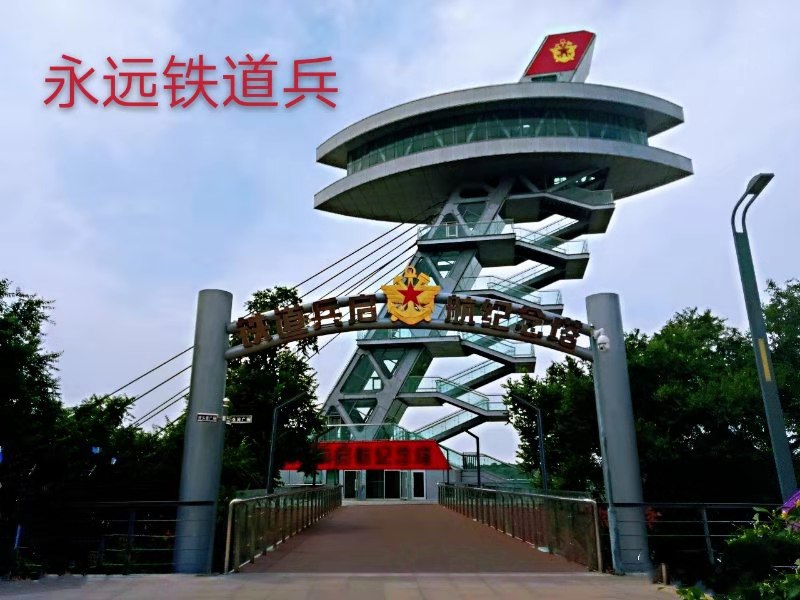
我是1971 年的兵,1970 年底征召并开始进行新兵训练。寒风里,我被送到铁道兵集训,当年全兵种新征女兵的训练营,地名叫顾册。

李东东
几百名女兵集中在一起,穿着一样的崭新的鼓鼓囊囊的绿军装,戴着红彤彤的帽徽领章,兴奋,激动,新奇。大家很快熟悉起来,一交流,才知道各自的入伍经历彼此彼此,差不多都以为当年只招文艺兵。最终,大多数人不是文艺兵,也进来了。但是有一点微妙的差别,我感觉得到,那就是军队干部子女要轻松一些,神气一些,不论她爸爸是将军还是营长;而不大多讲话,特别是不提自己爹妈的身份、经历的,往往是地方干部的女儿。这是可以设身处地想像的,因为在当时,中央和地方机关,原来的领导干部,大多数还处在被“打倒”的状态。
顾册新兵营的生活是热闹、喧嚣、生气勃勃的。怎么住的房,一间屋多少床,我已想不起来了。但爬冰卧雪的艰苦训练,管饱管够的新鲜粗粮,使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女孩子,个个脸上红扑扑圆鼓鼓的,这可是有照片为证的。不过,新兵时期的照片都是黑白的,那红扑扑的脸,表现在照片上,便是如秋菊一样冻得发僵、色泽略深的土妞妞样。
新兵训练时出的洋相,也无法一一尽述了。一个“动作要快”,就把我们这些学生兵,折腾得人仰马翻。都知道兵贵神速,军人,特别是战场上的军人,快五秒,慢十秒,可能就决定成与败、生与死。因此,训练中的收获,可以说表现在方方面面;而洋相的时候。例如,起床号吹过几分钟,你得穿好军装,整理好内务跑到操场;熄灯号吹过几分钟,你得钻进被窝,关闭电灯不能有声响;要在几分钟之内,把三横两竖的背包,打得平平整整;要在几分钟之内,把叠成“豆腐块儿”的军被,捏得有棱有角……
最尖端的是紧急集合。那天晚上我们已暗地里探到了消息,大家都兴奋得睡不着觉,想悄悄地等。但是“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排长毫不留情地监督巡查各班,不得和衣而睡。结果到凌晨三四点了,再能熬的也睡着了。寂静的雪夜里,凄厉的紧急集合号吹响了!霎时间,营房里炸了窝,个个摸着黑喘着粗气穿衣服、打背包,抓自己的枪。
这时候,原来的设想、程序、步骤……全然不复记忆,只听见床底下的脸盆,被踢得乱响;上铺下来的找不着鞋子,急得直叫;下铺打背包的人,打了一半儿,拽不动了,才发现背包带另一头,被邻床扯着正在打另一个背包!什么三横两竖、见棱见角全顾不上了,就听得外边传来排长的哨声,急促的口令,还有操场上,压得低低的整队声……
不管怎样,每个人都穿上了军装,带上了背包,扛着自己的枪,在暗夜里一个接一个跑完了全程。天亮了,回到营区,大家喘息未定,互相看看,不由得笑得喘不过气了:有背着背包的,也有根本没打好,而夹着跑了一路的,听说还有人被松下来的背包带绊了跤;帽子,有人都没来得及摸摸帽徽,把帽子戴反了;鞋子,有左脚右脚穿了不一样大的;居然还有那穿成一顺儿的,连累另一人也穿成一顺儿,拧着脚也能行军跑路!

李东东与战友在学院操场毛主席像前合影
除了练好射击、投弹这些项目外,我比较得意的是,敬一个标准的军礼。因为只有受过军人的训练,才知道什么是大臂端平、指尖齐眉的标准军礼;而如果肩臂不平,手指一翘,便是《南征北战》中“张军长李军长”们的国民党式军礼了。
我早想好了,春节放假回家,要像排长说的那样,给亲朋好友敬一个标准的军礼。这接受我第一个军礼的人会是谁呢?多半儿是妈妈,但爸爸也可能回家过年呢,若是姐姐哥哥都能回来,那就太好了。反正,我一定给第一个见面的人,敬一个神气的军礼!
多么简单又美好的愿望啊!就在我掐着指头盼春节的时候,一个突然的消息,使我的愿望变成了梦想。妈妈托人捎信儿,不让我回家过年。如果新兵营春节不留人,就是回京也不能回家!这简直太意外了,对一个历经周折穿上军装的新战士,对一个渴望父母温暖的小女儿。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作为一个新闻界“走资派”的子女,是在父亲没“解放”的情况下参了军。当年秋,中央刚刚开了九届二中全会,成为党内又一次路线斗争。而不知铁道兵学院怎么有人,把我的入伍与那个领导连起来了,有的传说是我父亲的老上级,有的则说我是的“黑侄女”。本来爸爸就没有“解放”,我们这些落难子女,是因了父母的敢负责任的老战友,才得以入伍的,而如果这使你得以入伍的因素再出岔子,那你的日子便真要雪上加霜了。
妈妈不但风闻了部队那边的周折,还听说报社这边的造反派有查问“走资派”子女入伍的动向。在她的感觉里,如果两边的麻烦一碰头,很可能我这兵就要当出毛病。说白了,就是当不成了。所以,我回到北京却不能回家,只能按妈妈给我的地址,住到了她的一个亲戚家里。亲戚在北京卫戍区工作,是军队干部并且正在“支左”,家里是很安全的。
敲开亲戚家的院门时,迎着来开门的人,我不由自主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开门的,是他们家的保姆;我的第一个军礼,就敬给了这位山东口音的老阿姨。
不记得为什么妈妈当天不能来看我,我非常想念妈妈,有一肚子话要说。于是像《红灯记》里李玉和与表叔“粥棚接头”一样,我和妈妈约定在王府井南口见面。昏暗的冬夜里,母女俩在大街上相会,望着自己穿着新军装却不能回家的小女儿,妈妈百感交集。我们不能一同回到近在咫尺的家,也不能让社址就在王府井的报社造反派看见,就悄悄地沿着王府井大街的东侧,冒着凛冽的寒风,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南……

李东东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作大会发言
人们都说时间会磨平一切,这种意思,也没少记述在古今中外的圣贤之书里。但是对此要有真正的体会,则一定是自己经历了,并且在很久以后,心情平复的时候。今天,当我回忆当年的一切,感到那么幼稚、有趣、有意思,可这轻轻的“有意思”三个字,所涵盖的那五年岁月,对于那个年代一个父亲受冲击的干部子女,当时,却常常感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五年从军路,扎扎实实培养了我服从指挥、雷厉风行、拉出来能打、打就得打赢的作风,这是足以让我受益终生的财富。我在回到地方后,得以比较快地适应不同的工作岗位,还是因为,我也曾是一个兵。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