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1969~1970 那个跨年的冬天
原创 |铁道兵张衍海
4
元旦前,新兵一连又把岀墙报的任务交给了我,这一次的任务很重要,因为新兵团要组织一次各新兵连墙报大评比;再加上过新年,当然要搞得像模像样一点。为了确保完成好任务,夺得好名次,连里让辛贵全给我当下手,做好配合工作。辛副班长的积极性非常高,满口答应下来。有人在场的情况下,他舞文弄墨的,好一阵忙活,整的好像他是主角我是配角一样。以前对他还不算很了解,通过近距离接触,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人。
我白天和别的新兵一起训练,晚上就在我们新兵一连住的四层走廊里铺开了摊子,在四十度的电灯泡底下写写画画。
这一天的晚饭后,是五连的女兵洗澡。女兵们三三两两地端着盆下楼的时候,有男兵带电的目光追逐着,送出好远。这一切,我并未察觉,只是有点感应,不知咋回事。
过了些时侯,也就一个小时左右,我感到脖子有点酸,抬了一下头,猛然看见有一个小女兵站在近处,正出神地看着我连写带画。我看她的时候,她也正看着我,目光交汇,只是一刹那。
“你好,我叫严冬雨。你呢?”
“哦,你好,我叫路远。”
“上两次,出墙报的时候,我就看到你了……”
“是吗?”
“你们的墙报,出的真好!”
被女兵夸,我还是第一次,感觉有点不好意思。我迅速扫了她一眼,扎着两根小短刷,刚洗过澡的缘故,还没来得及梳成辫子。脸是白里透红的,长得很标致,讨人喜欢的样子。好像在哪儿见过,又不确定。
那个叫严冬雨的女兵,用手摸了摸一个用完了的广告色瓶子,试探着问:“这个,借给我好吗?”
“你想要,就拿去吧。”
“谢谢!”
那个女兵把瓶子放进她端着的盆里,还用毛巾盖了一下,莞尔一笑。走了几步又回头,还是一笑,天真烂漫的样子。

不知不觉间,天就慢慢地亮了。我的任务也已基本完成,只等着新兵一连指导员钟守良前来验收。其实,验收只是一个形式,无关紧要。在我连夜挑灯大干的时候,钟指导员已经来过几次,每次都把探头探脑想看稀奇的那些新兵给撵回房间睡觉去,而他自己则默默地站在我身后,看我构图,调颜色,描描画画。这个时候,他虽然很少说话,眉宇间和嘴角上,都已挂上满意的笑丝。
钟指导员来过的这几次,辛贵全都没有在场。最后一次,他问:“辛副班长呢?”
我正忙着画最后的几笔,不假思索地答道:“可能他,打开水去了……”
“深更半夜的,打什么开水?”
“哦,我也不知道。”
指导员这一说,我倒是懵了。钟指导员没再说什么,转身到各班寝室看了一圈。在三班寝室里,他看见辛贵全睡得正香,呼噜声和在火车上时一个样……
钟守良是河南焦作人,1966年当兵,中等身材,相貌英俊。去年在老部队被提拔为排长,接新兵之前又被提升为副指导员,在新兵连里任指导员。我就是他亲自接的兵。在成功地运用了迂回包抄战术,粉碎了生产大队一干人的扣留企图和化解了百尺中学校方的百般挽留之后,钟指导员如愿以偿,把我这个刚当上民办教师才半年的回乡知识青年挖走了。
我能想象得出他当时是何等的兴奋,那必是一种心理和精神的双重胜利的感觉。我想象不出的是,已然获得双重胜利的钟指导员,又是如何在分配新兵的名单上再一次如愿以偿、把我归到他的名下,以至于达到神不知鬼不觉的程度……
钟指导员审慎地看着我花费了一夜的辛苦完成的作品。他压抑着内心的想法,是好是赖啥也没说。在吹响了起床号别人都在忙着整理内务的时候,他发话了:
“路远,快把你画的那张画卷起来,不要往墙上贴。”
我大惑不解,以为这画有什么政治问题,心惊胆战。
随后发生的情况是,钟指导员又让新兵一连出墙报的二号种子选手辛贵全接替我。他花了大半个白天的时间,重新画了一张报头,替换了我画的那一张。辛贵全早就跃跃欲试了。
无奈,他的绘画底子不咋地,只能临摹我画的原作,水平明显差一大截。
从1966年初夏到1968年深秋,整整两年半,我是一中红画兵的人,三个喜欢画画的同学,跟着两位美术教师,出画刊、办展览、绘伟人像,天天练这个,等于上了三年美专。他辛贵全一一三中的一个逍遥派,哪里有这番经历?“瘸子堆里拔将军”,在新兵团各连墙报评比中,新兵一连的墙报依然获得“第一名”的显赫成绩。
果然不出所料:赢得喝彩的不是我,而是辛贵全……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生活结束了。日子过得太快,来不及停留,来不及等待,甚至连遐想和回味都舍不得给你,更容不得你走过之后再回过头来寻找。

下一步要面临的,就是每个人不同的去向。不同的岗位,不同的选择,正在远处招手。多像铁路的道轨,延伸向前,不知道彼此在前面的某个地方,还有没有交汇点?若是没有,那就只能离别了,分开了一一何年何月何日见?渐行渐远渐无书。宣布命令的那一天,终于到了。
辛贵全被分到了团电影放映组。
而我呢,将要跟着钟守良到他原先的老部队一一铁J师钢一团一营二连,这是一个典型的施工连队。
老天有情,在我们将要离开的头天晚上,仿佛想给我们送行,纷纷扬扬地下起了这个冬天最大的一场雪,也可能是最后的雪了。五连的女兵们像是串通好了似的,抑或是通情达理的连排干部们有所通融,她们在楼前的院子里尽情地撒欢儿,扔雪球,堆雪人,跟一伙孩子没啥两样。男兵们只能隔着窗户往外看,尽管羡慕的不得了,眼馋得不行不行的,可是没有一个人敢下去和她们一起玩。这是部队不成文的规定,男兵和女兵之间要保持距离,但分寸如何把握,谁也拿捏不准。
辛贵全压抑不住身心的躁动,有点抓耳挠腮了。无奈连里看得紧,众目睽睽之下,他也不敢冒这个险,只能硬憋着。
钟指导员到各个寝室来回走着,看看大家都在忙什么。除了窗户口上的少数人之外,大多数新兵思想还比较稳定,情绪正常,有的在给家里写信,有的在翻日记或者读毛选。过了这一夜,明天就出发了,整理行装和打背包都是几分钟的事儿,新训期间演练过多少次了,所以今天晚上不用慌。唯有身为老兵的各班班长,知道排长们刚到连部开过会,料定今晚十有八九还要搞一次紧急集合。此事非小,但是又不能向外透露。心里头战备那根弦,时刻紧绷着……
吹过熄灯号,一切都安定下来。楼前多了几个大雪人,像是在给我们站岗。雪片飘零复飘零,无声,无息。我忽然想到那个女兵的名字,雪片不就是严冬的雨吗?假如有一天要走向冬以外的季节,雪人便会消失,与遍野的积雪一起,化成一河春水,波波溪流,缓缓地,缓缓地,流过那一段旧日时光……
一夜无事。
起床号把大家叫醒。新的一天,也是一条长路的起端。到老部队去,不坐火车,没有汽车,只靠两条腿,这就是拉练。新兵们都不知道,新兵团取消这个晚上紧急集合的决定,是团首长临时做出的。爱兵,是部队的传统。出发之前,马上要离开新兵训练住过的那幢红色墙体老楼的时候,在楼梯口遇见了严冬雨。这让我有些意外,又有些期待,说不清也理不开的情愫,无法释怀。
她是在等我。
此时此刻,已经背好行装准备走了。她被分到哪里了?
见面之后,严冬雨从肩上斜背的挎包里取出一个用手帕包裹的东西。打开手帕,原来是个用比铅笔芯细点的彩色塑料绳精心编成外套的玻璃喝水杯,她小心翼翼地递给我。
我一下子就认出来:那玻璃杯,正是被她“借”走的广告色瓶子……
两只清澈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一切都措手不及,什么都忘了说。
几秒钟的定格,世界仿佛凝住了。但是,时钟在走,钟表的指针剪断时间的时候,比任何锋刃都要锐利。
几秒钟后,她挥挥手,转身离开。因为要追赶队伍,她不得不一路小跑。
飘一阵停一阵的雪花还在下着,被白雪装饰起来的城市和街道披上层层白纱。一行脚印似在白纸上刚写的诗,不见开头也不见结尾,让品读的人浮想连翩。
记得在一本书里,是这样写的:人生,就是人与人相遇。有些人遇见了,或擦肩而过,或形同陌路。而能同你走一程或走到底的人,终究还是有,遇见了不会忘,分别了还能见……
一一这会是真的吗?

张衍海版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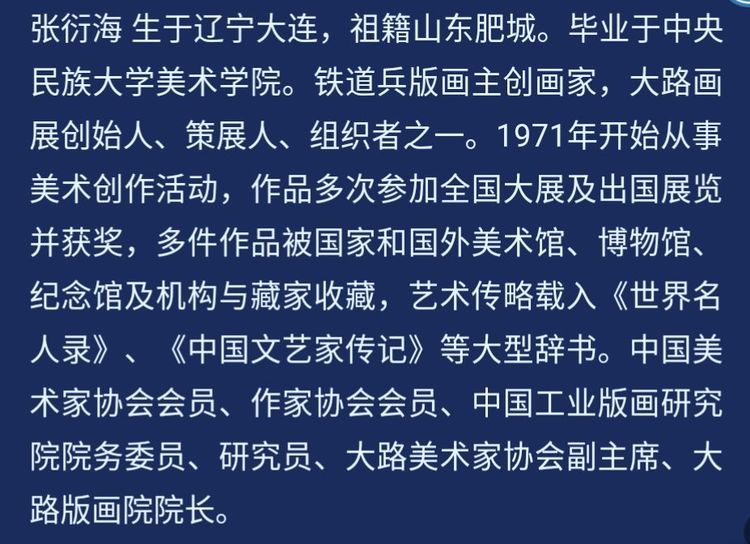
未 完 待 续
编辑:向日葵